半个月后,我补完膜,作为礼仪小姐,如愿出现在警示教育基地落成的揭牌仪式上。
这天,何牧深穿了一身警服,正襟危坐在最中央的位置,不需刻意渲染,气场特别强大。
肩章是两杠三星,彰显他身为市局副局长,高高在上的身份。
白衬衫打底,领口和领带一丝不苟,他左手边放着警帽,这会儿正在做工作报告。
他鲜少停顿,也很少去看秘书事先为他准备的发言材料,这一切对他来说似乎习以为常,磁性的嗓音,从听筒里低沉传来,格外好听。
不是没有见过男人穿警服,但何牧深绝对是我见过穿警服最有味道的一个,一种不到他这种地位和年龄,根本无法企及的成熟味道。
不知是不是我打量的目光过于直接,何牧深似有感应,视线朝台下看过来,近乎出于本能,我低下头,即便做好了和他碰面的准备,或许是太刻意,心虚又紧张。
等到揭牌环节,旁边的人捅了捅我,“嗳,想什么呢?揭牌了。”
我慌乱“哦”了一声,穿着高跟鞋,和其他三名姑娘,捧着《警监协同合作书》和签字笔走上台。
我把协作书自何牧深身后放到他面前,收手时不经意擦过他耳边,他扭头看我,我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看我,只当方才的行为是不小心之举,退到后面。
好在递签字笔的姑娘迎上去,何牧深只是堪堪瞭了一眼。
等再去收协作书,我故意去收市监察委主任的那份协作书,如我所料,何牧深朝我这边看来,我再次假装没看到,错开视线。
接下来没有我们礼仪什么事儿,我下台后,去后面化妆间准备换衣服。
这时,一位西装革履的青年找到我,问可不可以耽误我两分钟。
我迟疑了一下,但没有拒绝。
等到了无人的地方,青年拿出来一张名片给我,直接开门见山。
“顾小姐,我们领导今晚想请你吃个宵夜,如果方便的话,你打电话联系我。”
青年的话什么意思,再明显不过。
我接过名片,问他:“哪个部门的领导?”
对方说黄主任。
也就是市监察委那个黄主任。
我没缘由的失落了一下。
但想想也是,何牧深要是这么轻易就能上钩,哪至于成为红姐口中最难啃的骨头啊!
我没有拒绝,只说:“我考虑一下再联系你。”
与何牧深的这次偶遇,就这么不了了之,我没有再看到他,就像平静的湖面起了淡淡的涟漪后,再次恢复到平静,不见任何水花。
回到化妆间,琢磨再三,我打电话给青年。
“不好意思,我今晚答应与何局长吃宵夜了,麻烦你替我和黄主任说声抱歉。”
挂断电话,我人软在椅子上。
不是我故意给何牧深找麻烦,是我这种女人,在他们这些大人物之间压根没有立足之地。
对于黄主任,要么从,要么不从。
而不从的后果,我根本没有办法承受。
红姐说有个小姐妹仗着被一个副处级干部包-养,就自命不凡,开罪了一个副局级领导,最后落得个被丢到工地,被一群农民工轮干,盲肠都被干漏了的下场。
听说那个口口声声说喜欢她的副处级干部,连个屁都没敢放,为了自己以后的升迁之路,特意大摆宴席,向那个副局级领导赔礼道歉。
我拿何牧深搪塞,不过是在赌。
赌黄主任不敢和何牧深争。
也为着何牧深三分薄面,不敢为难我!
回出租房的路上,红姐打电话给我,声音很急,说今晚有个晚宴活动,要代替一个生病的小姐妹,问我行吗。
和红姐打交道半个月,她知道我性格如何,碰上临时救场的事儿,从不主动向我开口,今天若不是不得已,找不到顶替的人,绝不会打电话给我。
像是想到什么,红姐又说:“你要是今天不方便,我问问别人。”
“不用。”
我叫住红姐,“今晚晚宴,我可以去。”
红姐多精明一个人,没有追问,也没有安抚我,只是默了几秒后说:“很多事儿,别人怎么劝都没有用,只有碰了壁,撞了南墙,自己就知道回头了。”
让我对何牧深死心吗?
如果不是阮玟的未婚夫,我可能在第一次见面后,就让一切划上休止符了。
但偏偏有一种情绪,叫不甘心。
我没有多言,问了红姐酒店位置和时间。
晚上七点,我作为女伴,陪在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身边,出席粤湾一家能源企业主办的,以“绿色粤湾”为主题的商业晚宴。
自然资源厅的梁副厅长是个年近六十,即将退休的老头子,长得不算恶心,但却是个变态好色的主儿。
红姐说,肖彤今晚没法儿陪他出席晚宴是因为昨晚两人玩S-M,他把肖彤吊在灯管上打,打的人遍体鳞伤,走道都费劲儿,实在没有办法出席今天的活动。
红姐让我和梁副厅长来往,多加小心。
许是大庭广众之下,梁副厅长对我并没有什么过分之举,进到宴会厅后,只是带着我四处交际攀谈,期间,我充当陪衬的角色,不多言,也不骄矜,做漂亮的花瓶,给梁副厅长长脸。
忽的,我感觉到两道灼热的目光落在我身上,目光睇过去一瞧,心弦“咯噔”一颤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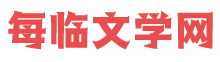
 连载中
连载中 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