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个月发粮票布票的日子,丈夫周建刚都会带点“新奇玩意儿”回家让我开眼。
这个月初八,他提干当上小组长的庆功酒刚过,就领回来一个烫着卷发、穿着喇叭裤的年轻女人。
粮站发的的确良布料刚到手,我还没捂热。
周建刚就指着那布对我说:“秀芹没身体面衣服,你把这布给她扯了做身新衣裳,再把你姥姥留的那对银镯子给她戴,她手腕细,戴着肯定好看。”
“对了,她刚从城里来,我们这儿的活计不大懂,你往后多带带,特别是咋伺候男人。”
院子里纳凉的邻居伸长了脖子,屋里婆婆和小姑子也竖起了耳朵,等着看我这个乡下婆娘的笑话。
我攥紧了衣角,指甲掐进肉里,第三次跟他说:“周建刚,我们离婚吧。”
周建刚像是听了天大的笑话,吐掉嘴里的瓜子皮,吊着眼梢看我:“陈望秋,你又来这套?这话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,比纺织厂的噪音还烦人!”
“你要真有种离婚,我把这凤凰牌自行车给你!”
院子里爆发出一阵哄笑,婆婆撇着嘴骂我“不知好歹的玩意儿”,小姑子翻着白眼说我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离了我们家看谁还要你”。
他们哪里晓得,这是我第三次说离婚,也是最后一次。
1
所有人的目光都黏在我身上,带着看戏的、鄙夷的、幸灾乐祸的。
连那个叫秀芹的年轻女人,也拿手绢捂着嘴,咯咯笑个不停。
“我赌她不出这院门就得哭着回来求建刚哥!”
“我压五毛钱,她不敢离!”
“我跟两毛!”
关于我会不会滚蛋的闲话,成了每次周建刚“开眼界”后的保留节目。
那些输了钱的邻居背后戳我脊梁骨,赢了钱的当面也甩脸子。
我扯了扯嘴角,心里骂自己窝囊,嫁过来五年,直到今天才算真正死了心。
“我压她离!”人群角落传来一个闷闷的声音,是住在隔壁院的老实人何平。
旁边的婶子赶紧拽他胳膊,“何平你瞎掺和啥?小心惹祸上身!”
我朝声音方向望了眼,只看到一个模糊的敦厚背影。
“周建刚,离婚报告我会写好,明天送到厂里,你记得签字。”
我提过两次离婚,但这是我第一次说要写离婚报告。
周建刚“嚯”地站起身,手里的搪瓷缸子顿在小桌上,发出刺耳的声响。
我没看他,转身回了我们那间逼仄的小屋,从箱底翻出那块崭新的的确良布料,还有那对被我擦得锃亮的银镯子。
布料是我省吃俭用攒布票换的,本想给孩子做件过年的新衣裳。
镯子是姥姥临终前给我的念想。
我把东西放在堂屋桌上,对着一脸得意的秀芹。
她叫刘秀芹,二十岁,皮肤白,眼睛活泛,一看就是城里见过世面的。
“这布你拿去做衣裳吧,料子薄,夏天穿凉快。”
“镯子有些年头了,戴的时候仔细点。”
“这家里的活计,洗衣做饭扫地喂猪,有什么不懂的,问婆婆和小姑子都行。她们住东厢房,你住西厢房这间。”
嫁到周家五年,伺候了老的伺候小的,如今还要伺候他外面的女人。
这个家,大大小小的女人加起来,快赶上生产队的娘子军了。
不过往后,这队伍里没我陈望秋了。
我最后看了眼桌上的东西,转身朝大门走去。
脚还没踏出门槛,胳膊就被一股大力拽了回来:“陈望秋,想走可以,把你身上这件衣服扒下来!”
“这是我周建刚扯的布,找人做的,你没资格穿走!”
纳凉的邻居还没散,闻声又围了上来。
我浑身的血在那一刻仿佛都冻住了,连牙齿都在打颤。
“你要我脱衣服?”
周建刚挑起一边眉毛,眼神凉得像腊月的冰溜子。“当年你未婚先孕,你爹妈不是把你捆着送到我家门口求我负责的吗?怎么来的就怎么走!”
“还是说你后悔了?也行,你跪下给秀芹把这杯茶端好了,我就当没听见你刚才放的屁。”
周建刚的婆娘和小姑子,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“我脱。”
没等众人反应,我已经开始解斜襟布褂的盘扣。
已是初秋,院里晚风带着凉意。
我里面只穿了件洗得发黄的汗布背心,风一吹,鸡皮疙瘩瞬间冒起。
布褂扣子解开,露出瘦削的肩膀和半截胳膊。
“哎呀!”有心善的婶子别过头去。
男人们的目光却愈发灼热。
只有周建刚,脸色黑沉得能拧出水,嘴唇抿成一条僵硬的线,唯有夹着烟屁股微微颤抖的指尖泄露了一丝异样。
布褂滑落在地,我穿着破旧的汗布背心和打补丁的裤子站在众人面前。
周建刚手里的烟烫到了指头,他猛地丢掉烟,抓起旁边搭着的脏兮兮的工装外套,劈头盖脸扔到我身上。
“陈望秋,你他娘的是不是疯了!”
“都看什么看!眼睛不想要了?今天的事谁敢出去乱嚼舌根,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!”
“都给我滚!滚!”
周建刚很少在外面发这么大的火。
“你敢离?你弟娶媳妇那三千块彩礼钱你家还清了吗?你娘常年吃药的钱你掏得起吗?”
“陈望秋,你信不信,只要我一句话,你娘家第一个跪在我面前求我别不要你!”
周建刚对我,对我娘家,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厌恶,根本藏不住。
他恨我家当年算计他,更恨我逆来顺受,丢了他“城里人”的脸。
“当年要不是你爹妈贪财,要不是你半推半就,我会娶你?我早就娶了厂长的女儿!”
“陈望秋,是你自己作践自己,毁了你这辈子!”
这些话,五年里他变着法子说了无数遍,我早就麻木了。
当年确实是我爹妈为了一点彩礼钱,强行把我送上了周建刚的床上。
见我不吭声,周建刚眉头拧得更紧。
他拎着我的胳膊,把我推到刘秀芹面前,指着桌上的茶杯:“给她端茶认错!这点眼力见儿都没有,活该当一辈子受气包!”
我再一次听话地端起了那杯凉透了的茶,递到刘秀芹面前。
或许是我太顺从,让周建刚失了兴致。
他一把夺过茶杯摔在地上,指着西厢房:“滚进去!看着就心烦!”
西厢房是我的房间,也是他和我的婚房。
他当着我的面,把刘秀芹拉了进去,反手锁上了门。
我被关在了门外。
2
夜里凉气重,我抱着胳膊蹲在冰冷的灶房门口,听着西厢房里传来的嬉笑声。
那里曾经是我的婚房,如今成了别人的安乐窝。
天蒙蒙亮,我就得起来烧水做饭,喂猪扫院子,伺候一大家子人。
饭桌上,婆婆把唯一的白面馒头夹给了刘秀芹,把黑乎乎的窝窝头推到我面前。
“吃吧,乡下人吃惯了粗粮,细粮该给秀芹补补身子。”
刘秀芹娇笑着,把馒头掰了一半递给周建刚,“建刚哥,你尝尝,真香。”
周建刚接过馒头,看都没看我一眼。
小姑子在一旁阴阳怪气:“有些人就是没福气,给她好东西她也留不住,活该啃窝窝头。”
我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稀饭,味同嚼蜡。
吃完饭,周建刚要去厂里上班,刘秀芹给他拿着洗脸水,挤好牙膏,又拿出我那双纳了半个月才做好的新布鞋。
“建刚哥,你看这鞋做得多好,嫂子手真巧。”
周建刚穿上鞋,随意地踩了踩地上的泥水,“嗯,也就这点用处了。”
他临走前,丢给我一把脏衣服,“下午洗出来,晚上我要穿。”
里面夹杂着刘秀芹的贴身小衣,带着一股陌生的香水味。
我拿着那些衣服去了河边。
冰冷的河水刺痛着我的手指,也一点点冻僵我的心。
下午,娘家托人捎来口信,说娘病得下不了床了,让我赶紧回去看看。
我心急如焚,跑回家想跟周建刚请个假,顺便借点钱给娘看病。
周建刚正躺在院里的藤椅上,让刘秀芹给他捶腿。
听我说完,他眼皮都没抬,“又装病?你娘那身子骨,我看比牛还壮实,准是又想骗钱!”
“这次是真的!捎信的人说娘咳得厉害,都咳出血了!”我急得快哭了。
“咳血?我看是装可怜博同情吧!”婆婆从屋里走出来,“我们家刚提干,正是用钱的时候,哪有闲钱给她看病?再说了,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,娘家病了关我们周家什么事?”
“建刚,我只借十块钱,等我下个月挣了工分就还你!”我放低了姿态,几乎是在恳求。
周建刚不耐烦地挥挥手:“没有!一分钱都没有!要去你自己想办法,别来烦我!”
刘秀芹在一旁添油加醋:“嫂子,你娘家就是个无底洞,建刚哥赚钱也不容易,你怎么好意思老开口?”
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,一片冰凉。
雨还在下,我没带伞,一路顶着雨往几十里外的娘家跑。
泥泞的路滑得很,我摔了好几跤,浑身都是泥水。
天黑透了,雨也越下越大,我浑身湿透,又冷又饿,终于撑不住倒在了路边的草丛里。
迷迷糊糊中,感觉有人在拍我的脸。
“望秋?陈望秋?醒醒!”
是何平的声音。
他打着手电筒,穿着雨衣,自行车停在一旁。
“你怎么一个人在这?还淋成这样?”
看到熟人,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,哗哗往下流。
何平没多问,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我身上,扶我坐上自行车后座。
“先去我家,喝碗姜汤暖暖身子,不然要生病的。”
他把我带到他家,一间比周家更破旧的小土屋。
他娘早年过世了,家里只有他一个人。
他给我烧了热水,煮了碗放了红糖和姜片的姜汤。
“快喝了驱驱寒。”
我捧着热乎乎的碗,眼泪又掉了下来。
临走时,何平从枕头底下摸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,塞到我手里,“拿着,给你娘看病,我这儿就这么多了。”
“我不能要!”我赶紧推回去。
“拿着吧,救急要紧。”何平把钱硬塞进我口袋,“以后有难处,就来找我,这是我家地址。”
他递给我一张写着地址的小纸条。
我捏着那几块钱和纸条,心里五味杂陈。
3
我拿着何平给的几块钱,又找遍了娘家所有亲戚,东拼西凑,也只凑够去县城的路费和挂号费。
爹用牛车把娘拉到县医院。
医生检查完,摇了摇头:“太晚了,拖得太久了,只能尽量维持。”
每天的医药费像流水一样淌出去。
我白天在医院照顾娘,晚上就去码头扛麻袋,或者去饭馆帮工洗碗,挣几个微薄的辛苦钱。
手上磨出了血泡,肩膀被麻袋压得红肿,腰累得直不起来。
可看着娘一天天衰弱下去,我知道这些远远不够。
我鼓起勇气,又回了一趟周家。
周建刚和刘秀芹正在院子里晒太阳,旁边放着一盘瓜子。
看到我一身狼狈地回来,周建刚皱起眉头:“你还回来干什么?不是说你娘快死了吗?”
“建刚,求你,再借我点钱,五十,不,三十就行!我娘真的快不行了!”我跪在了他面前。
这是我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跪他。
“没钱!”周建刚把脚从凳子上放下来,居高临下地看着我,“陈望秋,我早就跟你说过,你娘家就是个填不满的坑!我凭什么拿钱去填?”
刘秀芹嗑着瓜子,凉凉地说:“就是,建刚哥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,嫂子你不能总拖累我们啊。”
婆婆闻声出来,叉着腰骂道:“丧门星!一回来就要钱!是不是看我们建刚提干了眼红?我告诉你,我们周家的钱,一个子儿都不会给你娘家花!”
我看着他们冷漠的嘴脸,听着他们刻薄的话语,心一点点沉入冰窖。
我慢慢从地上站起来,拍了拍膝盖上的土。
“我知道了。”
我没再多说一个字,转身离开了这个我曾以为是归宿的地方。
回到医院,娘已经陷入了昏迷。
我守在她身边,握着她枯瘦的手,一夜未眠。
第二天清晨,娘在我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
娘走了,走得很不安详。
我甚至凑不够钱给她买一口最薄的棺材。
最后还是何平听说了消息,偷偷送来了二十块钱,又找了几个同乡帮忙,才勉强把娘的后事办了。
爹蹲在坟头,哭得像个孩子。
弟弟弟媳盘算着娘留下的那间破屋子。
这个生我养我的家,如今也彻底成了我回不去的地方。
我把娘留下的一只旧银簪子小心翼翼地贴身收好,那是她当年唯一的嫁妆。
回到周家时,天已经黑了。
刘秀芹正坐在炕上,手里把玩着一支银簪子。
是娘的那支!
“你从哪里拿到的?”我的声音都在抖。
“哦,这个啊,”刘秀芹抬起头,脸上带着挑衅的笑,“今天下午你婆婆打扫你那屋,从枕头底下翻出来的,说是个旧东西不值钱,就给我玩了。”
“还给我!”我冲过去想抢回来。
“凭什么给你?”刘秀芹把簪子举得高高的,“我看这簪子挺别致的,我要了!”
“那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念想!”我眼睛都红了。
“你娘?那个痨病鬼?”刘秀芹嗤笑一声,“死了就死了,留个破簪子有什么用?晦气!”
她说着,把簪子往地上一扔!
清脆的断裂声响起。
簪子摔成了两截。
那一刻,我脑子里最后一根弦,“嘣”地断了。
我什么也顾不上了,抓起炕边的鸡毛掸子,疯了一样朝刘秀芹抽了过去!
“我打死你!我打死你!”
4
“啊——杀人啦!”
刘秀芹尖叫着抱头鼠窜。
周建刚和他婆娘闻声冲了进来。
看到眼前的情景,周建刚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鸡毛掸子,狠狠掼在地上。
“陈望秋!你他娘的疯了是不是!”
他冲上来,扬手就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。
我被打得一个趔趄,撞在冰冷的墙壁上,耳朵嗡嗡作响,嘴角尝到了血腥味。
“她摔坏了我娘的簪子!”我捂着脸,嘶吼道。
“一个破簪子值几个钱?秀芹要是伤着了,我扒了你的皮!”周建刚眼睛通红,像要吃人。
婆婆扑到刘秀芹身边,查看她的伤势,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:“天杀的搅家精!扫把星!我们周家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娶了你!”
刘秀芹捂着胳膊上被抽红的印子,哭哭啼啼:“建刚哥,我好疼……她跟疯狗一样……”
周建刚看着刘秀芹胳膊上的红痕,怒火更盛,指着我的鼻子:“滚!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!”
“我偏不滚!”我梗着脖子,迎上他的目光,“周建刚,离婚!现在就写离婚报告!”
“离婚?你想得美!”周建刚冷笑,“你想带着我周家的种去找哪个野男人?我告诉你,门儿都没有!”
“孩子我自己养!跟你没关系!”
“没关系?陈望秋,你是不是忘了,你弟弟的工作还是我托人找的?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他滚蛋回家种地?”
又是威胁。
永远都是威胁。
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,突然觉得无比陌生,也无比恶心。
“周建刚,”我的声音平静下来,带着一种死寂般的冷漠,“随便你。”
说完这三个字,我转身走向门口。
这一次,没人拦我。
周建刚大概以为我只是又一次赌气回娘家,过几天自然会灰溜溜地回来。
他错了。
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,我停住了脚步。
从贴身的口袋里,我摸出了那张皱巴巴的纸条。
何平的地址。
还有那枚断成两截的银簪子。
我蹲下身,在老槐树下挖了个小坑,把断掉的簪子小心翼翼地埋了进去。
娘,对不起,女儿没能保住您的东西。
娘,女儿不孝,以后不能常来看您了。
我磕了三个头,额头抵着冰凉的泥土。
再抬起头时,眼里已没有半分留恋。
我站起身,辨认了一下方向,朝着县城的方向走去。
天快亮的时候,我走到了去县城的公路边。
一辆解放牌卡车停了下来,司机探出头:“妹子,去哪儿啊?”
我找到了何平留下的地址,是城郊的一个大杂院。
敲开门,是何平惊讶的脸。
“望秋?你怎么来了?”
“何平哥,”我看着他,鼓足了所有的勇气,“周建刚那里,我回不去了。”
“你能……帮我找个能干活糊口的地方吗?什么苦活累活我都能干。”
何平沉默了片刻,叹了口气,点了点头。
“先进来吧。”
后来我才知道,那天周建刚等了我一天,没等到我做好的晚饭。
晚上他去我娘家找人,才发现我根本没回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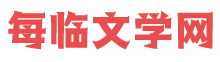
 已完结
已完结 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