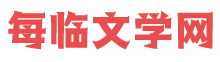《媳妇邓晓阳我叫李朝阳》 第1章 退伍回到乡政府,意外成为武装部干事 在线阅读
我叫李朝阳,东原地区平安县安平乡人,1983年参军,1985年光荣退伍。之所以说光荣,是因为我跟随部队在边境参加了战斗,并荣立个人三等功。虽说立了三等功,可赶上大裁军,回来不久,部队就改编了。对于脱离部队的农村兵而言,二等功可以安排工作,但三等功的意义不大。那时部队参军,农村兵安置的大原则是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,该种地依旧种地。
本以为这辈子就要与庄稼相伴了,退伍后我到乡镇武装部(我走的时候还是公社武装部)报到办理手续,命运的天平却在这一刻开始向我倾斜,自己也没想到,日后会成为大家口中的高级干部。
来到安平乡武装部,很是凑巧,武装部长李尚武也是转业军人,我们还是一个军的。他前些年以副团级转业到乡镇,担任我们乡武装部长。大裁军过后,军官都是降级使用,按说副团转业以前是要安排正科职位的。
得知我在连队干过文书,又是高中毕业生,既是战友又是老乡,李部长便有意拉我一把。我把自己在部队发表的一些文章拿给部长看,当时我们军办有一份《战旗报》,我在连队当文书时,经常发表一些豆腐块文章。拿出报纸时,部长眼睛都亮了,他说以前每周都会看这份报纸,自己也发表过不少文章,如今已经一年多没看到了,此刻看到《战旗报》,倍感亲切。这几份报纸上都有我写的文章,原本拿回来是打算向父母炫耀的,确实没想到,在这里能遇到老读者。
能写文章,又上过战场、立过三等功,武装部李尚武部长不禁称赞道:“小子,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文武全才。我这儿正缺一个干事,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帮忙?只是刚开始肯定不是正式编制,等合适的时候,咱向领导申请,看能不能把编制解决了。”
这般天上掉馅饼的好事,就砸在了我头上。就这样,我成了乡武装部的一名非正式工作人员。农村土地已实行承包到户,武装部最重要的民兵训练也不像从前抓得那么紧了。我当兵前,村里的民兵都要组织打靶,村里的民兵连长时常穿着一身褪色的军装。我当兵回来后,村里民兵的枪械都已上缴统一管理。
乡镇里有五六十人,作为农业大乡,这样的人数算多的了。除乡镇领导外,就是七站八所的工作人员。卫生院和派出所这些大单位不和乡政府在一起,其他像乡农机站、畜牧站、水管站、社事办都和乡政府一起办公。乡里看似有这么多人,可大部分都是三十多到五十多岁的“老人”,像我这种二十出头的只有两个,一个是党政办公室主任邓晓阳,另一个就是我。邓晓阳是去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乡镇的,分配来不久就担任了办公室主任。
作为办公室主任,晓阳手底下都是比她年长许多的人。在论资排辈的年代,邓晓阳这个外来户开展工作并不顺利。上面有乡镇领导,下面是不听使唤的老油条,所以办公室的工作常常都是晓阳一个人在做,好在那时事情不算多。
武装部和办公室的办公地点并不相邻。作为“权力”中枢的乡办公室,位于第一排的红砖瓦房里。而武装部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,武装部只有一间办公室,办公室里有两张桌子,一张桌子上落满了灰,另一张桌子上则散落着不少报纸和杂志。
在连队当文书时,我也算机灵,深知要进步关键在于处理好和领导的人情世故,所以就想着一定要和邓主任搞好关系。毕竟马军书记和张庆合乡长去县里开会、下乡,时常带着的就是邓主任。
邓晓阳个头不高,长相乖巧,对人热情,说话嘴甜。闲暇时,她会到李部长的办公室说些悄悄话。看着他俩低头嘀嘀咕咕,我心里不禁感慨:“这小美女可不简单,和书记乡长关系好也就罢了,连一个没进班子的乡武装部长,她都能把关系处得这么好。”
邓晓阳每次来都不会空手,只要我在,她都会从兜里掏出几颗奶糖丢在桌子上。这种糖在我当兵前从未吃过,直到在前线的猫耳洞里,偶尔会有奶糖和香烟送上来。我不会抽烟,战友虞家林他们分烟,我和几个不抽烟的人就分糖。同样的奶糖,却感觉味道不同,总觉得晓阳给的糖有一股子奶香气,也许这就是晓阳的味道吧。那个年代,别说乡干部,就是县里的干部也不一定能随时吃上奶糖,倒不是因为贵,而是小的供销社根本没有。
有一次,县武装部要一份报告,都是些琐碎小事,但需要咬文嚼字。我写好后,李部长感叹道,先不说你小子写得怎么样,就这一手钢笔字就是加分项。去吧,找晓阳盖章。
我写好报告后去找邓晓阳盖章,邓晓阳看了看我写的报告,一脸不可置信地说:“看不出来,你还会写材料,而且字写得这么好?”其实,我的钢笔字一直不错,军区组织的硬笔书法大赛,我还得过名次。
乡大院里能动笔写材料的,除了邓晓阳,还是邓晓阳。看到我写的报告,邓晓阳一边笑一边点头说:“没想到,李叔一个大老粗,还相中了你这么细腻的人。”说着就开始在兜里翻找,好一会儿才掏出一个奶糖来。“就这一颗了,给。”
我看着晓阳白嫩细腻的手,咽了咽口水,也分不清自己是馋糖还是馋人家的手。鬼使神差地伸手去接糖,这一下就触碰到了晓阳的手。两只手触碰的那一刻,一股电流贯穿全身。我看到晓阳仍在认真看文件,但感觉那一刻,晓阳脸上多了一抹绯红。
晓阳看得专注,我剥开糖,那熟悉的奶香气愈发浓郁。脑子一热,手一伸,低声说:“你吃。”这声音低得几乎自己都听不见。晓阳疑惑地看着我,愣了愣,笑着说:“借花献佛啊。”
那一刻,我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,根本不敢看晓阳。晓阳则看了看门口,见四下无人,倒是大方地说:“我手没洗。”说着张开樱桃小嘴,一下就从我手里把糖含住了。晓阳的披肩秀发落在我手上,那一刻,我确定,我馋的不是糖。
晓阳一边嚼着糖一边说:“李朝阳啊,我看你跟着李部长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要不这样,没事的时候你帮我写稿子吧。”“哎,哎,邓主任,只要您需要,尽管吩咐。”
时间久了,晓阳时常找我帮忙,写个通知、发个文件、报个简报,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。几项工作信息登上了县里的新闻简报,有那么一两篇还被地区的报纸刊登了。晓阳十分大方,只要有信息被上级采用,就会带我去喝一碗羊肉汤。要是赶巧她晚上值班,还会叫上李部长一起小酌二两。
没过多久,乡长和书记就认识了我,这让我备受鼓舞。有一次吃饭,晓阳说:“李叔,我这边忙着几个专项工作,能不能让朝阳搬到党政办,帮我几个月忙,用完我再还给你。”李叔说:“我没问题,不过你得找老马和老张点头。”晓阳说:“只要你放人,马书记和张乡长的工作我去做。”“你也得问问当事人同不同意。”晓阳给我夹了一筷子肉,问:“朝阳,你愿不愿意搬到办公室来?”我看看一脸坏笑的李部长,又看看一脸真诚的邓晓阳,说:“我服从组织安排。”当时,我心里也在想,能留到乡武装部已属不易,要留到办公室,难度多少有些大,不知道邓晓阳有没有本事把我留下。部长是过来人,笑着对我说:“我咋看你俩的眼神不太对劲,是不是咱武装部的这头猪要去拱白菜了。”
没过两天,李部长就通知我到办公室报到。我抱着几本书,拿着一些文件资料,搬到了邓晓阳对面的位置。本就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,又整天一起干活,渐渐地,我和邓晓阳的关系越来越亲近。一起去食堂吃饭、一起加班、一起在大院里散步。其实那时的晓阳,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领导,真正的领导是乡书记马军、乡长张庆合和武装部长李尚武。部长看到我们,总会悄悄地给我挤眉弄眼,意思不言而喻。
但我内心一直不敢倾诉心意,说实话,我有些自卑。那时邓晓阳是正式的国家干部,而我是一个不知能否转正的临时工。我家在农村,邓晓阳家在县城,虽说她从不谈及自己的家庭,但能看出,邓晓阳并非普通家庭的孩子。
可邓晓阳反倒比我大方,她是城里孩子,又读过中专,没那么保守。有时候同事们开我们玩笑,她也不怎么反感,依旧拉着我一起吃饭、一起散步。那时,我心里其实挺开心的,也给自己打气,人家女孩子都不怕,我一个上过战场的人怕什么。反正咱也没做什么,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但事实上,确实也没做什么逾矩之事。
很快,玉米熟了,农村进入秋收时节。大部分干部家里都有田地,包括乡镇、学校在内全部放秋假,只安排了少数几个干部轮流值班,我也回家掰玉米去了。我家离乡镇不远,只有两三公里,但家里房屋不多,我们五兄妹根本不够住,所以平时我都住在乡大院的宿舍里。乡大院的宿舍,除了值班的,住在这里的人并不多,我算一个,邓晓阳有时候加班也会住宿舍。
掰玉米时,有些玉米还没完全成熟,水分大,不能放太久,否则会发霉,所以会单独煮来吃。虽说比不上嫩玉米好吃,但也聊胜于无。掰了一天玉米,弄得一身臭汗,我到村前的大河里冲了凉,便吃晚饭。那时玉米、花生、红薯都成熟了,一桌子都是香气。
吃完后,我睡惯了宿舍的大床,实在不想和二哥正阳挤在一张床上。于是,我装了一些玉米、花生放在自行车上,准备去乡大院宿舍睡觉,这些玉米、花生自然是带给邓晓阳的。她今天值班,明天就可以休息了,我把这些放在公共汽车上,让她带回家。
趁着夜色,我骑着车,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晓阳,车子越骑越快,十多分钟就到了乡大院。此时才九点多,邓晓阳有个习惯,只要值班就睡得很晚,晚上喜欢猫在办公室看小说,她说只有这个时间,才感觉生命是属于自己的。
我看办公室没人,就打算去宿舍找她。我喊了几声,却没人答应,难道她回去了?应该不会,办公室的门没上锁,杯子里还有热水。我在宿舍门口敲了敲门,里面传出开门的声音,邓晓阳开了门,“朝阳,你来了,我有些不舒服。”邓晓阳头冒虚汗,声音沙哑,一脸虚弱。
“怎么会这样?”“不知道,昨天降温了,兴许是感冒了。”我在前线时学过一些基本医护知识,测温是最简单的。我用手摸了摸邓晓阳的额头,滚烫。“必须先降温。对,去乡卫生院,那里有值班医生。”
邓晓阳摆了摆手说:“四肢无力,头疼,走不了路。”乡大院原本有一辆县里淘汰的吉普车,虽说不知道传了几手,但在当时也是稀罕物,是县委作为乡镇企业改革先进乡的一等奖奖励给乡里的。可晚上乡长和书记都住在县城,所以车也在县城。这种情况,又是晚上,也不敢让邓晓阳坐自行车。我说:“也别讲究了,我背你过去。”
邓晓阳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,脸色一红,有些娇羞,但还是点了点头同意了。乡卫生院离乡大院不算远,不到一公里。邓晓阳站起身,看着我一米八的个头,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一把抓住我的肩膀,站到凳子上,趴在了我的背上。一股淡淡的香气钻进鼻孔,长这么大,我还从未这样背过一个女孩,心脏扑通扑通直跳。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,我背着邓晓阳,临出门时,还不忘一脚勾着把门关上。
走出乡大院,路上静悄悄的,秋风拂面,空气中弥漫着酒糟的味道,那是不远处的高粱红小酒厂正在酿酒。高粱红小作坊从我小时候记事起就有了,门口的木门已经包浆,曾经的私人作坊如今已成为安平乡的乡镇企业。农忙时的乡村,大家劳累一天,晚上喝上二两高粱酒,浑身舒坦。
没有路灯,也没有车灯,只有头上皎洁的月光和从谁家大院里传来的狗叫声。按说平时背一个人不算什么,毕竟五公里越野我在连队都是前三名。可那天掰了一天玉米,手本就有些酸,不知不觉中,我也冒了虚汗。这不算远的距离,平时觉得没什么,这会儿却有些气喘吁吁了。不知不觉,为了不滑下去,邓晓阳勒住了我的脖子,我的手也不自觉地托起了邓晓阳的屁股。
就这样走了几十米,邓晓阳忽然打了一下我的头,在我耳边轻声说:“坏蛋,手往哪儿放。”这时,我才意识到手放在了人家姑娘的屁股上。我把邓晓阳往上背了背,说:“我的邓大主任,你别打了,我也快累趴下了。”邓晓阳又打了一下,说:“要不你抱着我吧。”我确实这个姿势手没了力气,就把邓晓阳放下。看着晓阳的眼睛,我一时间方寸大乱,那种感觉,用小鹿乱撞来形容再贴切不过。我左右看了看,确实没人。
晓阳看出我的担心,笑了笑说:“咋,抱不动?”我咽了咽口水,一把就把晓阳抱了起来。晓阳两手勒住我的脖子,走了没几步,头就十分自然地枕在了我的肩膀上。我心里暗自嘀咕:抱着可比背着沉啊!但心里实在舍不得放手,还不时像做贼一样,生怕遇到什么人。就这样,我背一会儿,抱一会儿,终于到了乡卫生院。
乡卫生院的值班医生被喊起来,还满脸怒气,看到来的是邓晓阳,脸色好看了许多。量了体温,一看快40度。医生经验丰富,马上打了退烧针。但退烧针效果没那么快,还需要物理降温。我找了个盆子,向医生要了温开水,也顾不上许多,就帮着邓晓阳擦了擦额头和脖子。换了七八次水,熬了一夜,等到第二天,邓晓阳的烧总算退了。人退了烧,精神状态就好了,看着我咧嘴傻笑。
在医院休息了一会儿,邓晓阳说想回家,不想在医院住了。于是,我带着一袋子花生、玉米,送邓晓阳回家。在公共汽车上,邓晓阳依偎在我的肩膀上,就这样,我俩稀里糊涂确定了恋人关系。等到下车,我肩膀上扛着玉米和花生,一手拉着邓晓阳,走着走着,怎么感觉越来越熟悉。最后忽然想起来,这条路不正是通往县委大院的路吗?
邓晓阳说:“这就是我家,县委大院。”这时我才知道邓晓阳的父亲是副县长,就是那个我在简报里经常看到的人。其实这一点我早该想到,哪个中专生毕业一年多就能直接担任党政办主任呢。知道邓晓阳的父亲是副县长,我放下花生、玉米就打算走。邓晓阳拉着我说:“敌人都不怕,还怕自己的同志?你难道让我一个人扛着这些东西回家?”看晓阳一脸坚定,我心想,大不了被撵出来,能怎样。
等到家门口,晓阳敲开门,还好是她母亲开的门。阿姨看到我明显一愣,但不愧是领导干部家庭,马上露出笑脸让我进门。当天不是周末,邓晓阳的父亲作为县城干部,不放秋假,所以不在家。阿姨给我泡了茶,上下打量了我几眼。晓阳可怜巴巴地说:“妈,我昨天发烧快40度,是我这个同事朝阳送我去的医院,今天又送我回家来了。”阿姨笑眯眯的,十分热情,说了些客套话。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,中午阿姨留我吃饭。阿姨十分利索地进了厨房,嘱咐道:“晓阳,陪你同事聊聊天。”我本打算去厨房帮忙,被阿姨拒绝了。
不得不说,阿姨厨艺精湛。中午,不一会儿就做了四菜一汤。聊天时,阿姨话里话外都是问我的家庭、过往。当得知我上过战场,还在部队立了三等功时,阿姨还专门敬了我一杯茶水。下午,邓晓阳又送我到汽车站。秋假这几天,我对她朝思暮想,就连干农活时也心不在焉。我从未如此盼着上班,当然,盼着上班是为了见到邓晓阳。
秋假结束,邓晓阳来上班,一见面,趁着没人,我们先抱了抱。那时大家提倡自由恋爱,但婚姻大事,还是遵循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,自由恋爱的少之又少。所以在旁人眼里,我们还是和普通同事一样,甚至还刻意保持距离。
过了没多久,邓晓阳告诉我:“朝阳啊,我妈偷偷跟我说,我爸找机会会来看看你。”听到副县长要来看我,我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,但还是故作镇定地说:“来就来吧,县长又不吃人。”
说曹操,曹操到。当天乡里便接到通知,常务副县长邓牧为要来乡里检查工作。书记和乡长立刻带领全乡干部职工打扫大院卫生。实际上,一般的县领导前来,倒不必如此大动干戈,但常务副县长亲临,乡长和书记哪敢有丝毫懈怠。
第二天一大早,乡党委书记马军和乡长张庆合便早早候在了乡大院。约莫10点钟,一辆吉普车缓缓驶入大院。这位常务副县长气场强大、派头十足,平日里威风凛凛的书记和乡长,在他面前也变得格外谦逊,尽显平易近人之态。
邓县长组织乡班子开了会,之后又单独留下书记和乡长交谈。随后,乡长来到办公室,把我叫了过去。此时,书记和乡长都已离开,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与邓晓阳的父亲——邓副县长,面对面。
邓副县长上下打量了我一番,开口说道:“你目前还没有解决编制身份问题,年轻人,应当以事业为重。我现在不是以副县长的身份和你交谈,而是以晓阳父亲的身份明确告诉你,你和晓阳的事情,我不同意。”他语气坚定,不容置疑,没给我丝毫开口辩驳的机会,话一说完,便端起保温杯,转身离去。书记和乡长热情挽留他吃饭,邓副县长婉言拒绝,没有留下。
我走在回办公室的路上,听到同事们在一旁议论纷纷:“这邓副县长今天咋没留下来吃饭呢?往常来可都是要吃的呀。”
回到办公室,晓阳满脸焦急,迫不及待地问道:“我爸爸跟你说了什么?”我看了她一眼,心中五味杂陈,艰难地吐出几个字:“咱们还是分手吧,咱俩在一起,真的不合适。”晓阳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,带着哭腔说道:“我不管,我绝不分手。”
此后,书记和乡长也时不时找我谈话,话里话外都是在告诫我,作为一个临时工,千万不要得罪领导,别把自己的前程给耽误了。为了避嫌,我主动提出调回武装部。说是主动申请,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,这也是领导的意思,只不过主动申请这种说法,听起来更顺耳些。
李部长看着我,语重心长地说:“大丈夫何患无妻。邓晓阳确实很不错,但你俩的差距实在太大了。她父亲下一步接任县长,基本已成定局。你还是脚踏实地,先把正式身份解决了才是正途。”
在那段日子里,我总是刻意躲着晓阳。即便如此,每一天我都备受煎熬,只要一天见不到她,心里就像有猫在抓挠一般难受。
到了1986年春天,邓晓阳找到我,告诉我她已经和父亲摊牌,说两人彻底分手了,还说她父亲愿意在我身份问题上提供帮助。我说道:“不用了,我想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。”晓阳轻轻敲了一下我的脑袋,嗔怪道:“你别犯傻了,事情哪有那么简单。没人帮你说话,谁会给你办呢?”
就这样,在1986年夏天,我终于正式解决了身份问题,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。
彼时,改革开放成为全国热议的话题。然而,我们身处内陆地区,只是听闻沿海地区发展迅猛,却难以真切体会到究竟快到何种程度。
1987年,我的吴越战友虞家林到省城出差,特意坐大巴车辗转来到我的家乡。这些年,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。当年在连队时,我们并肩作战,我的三等功便是与他一同立下的,我们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。
战友兴致勃勃地跟我讲,他在魔都做外贸生意,据他描述,魔都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,而我们这边依旧贫穷落后。他的外贸公司发展得如火如荼,正处于扩张阶段。他此次前来,一是为了和我叙旧,重温昔日的战友情;二是询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干一番事业。我当时脑子一片混乱,便说要回家商量商量。战友在我这儿住了两天,临行前留下名片,还叮嘱我,只要我想去,随时去找他,还笑着说“苟富贵,勿相忘”。
我静下心来仔细思量,自己虽说解决了身份问题,但在这乡政府,和邓晓阳在一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眼下,邓晓阳因为我俩的事,一直和她父亲怄气,上面调她去别的地方,她坚决不去;组织提拔她,她也拒绝。我心里想着,倒不如出去闯荡一番,这样对她、对我或许都好,也能让她找一个更般配的人。
于是,我下定决心,找到书记和乡长,提交了辞职报告。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的轰动,远远超过我入职之时,毕竟那时还没有“下海”这种说法。
乡长和书记轮番找我谈话,苦口婆心地劝我,说乡政府虽说工资不高,但好歹是吃公家饭的安稳工作,我跑去魔都,简直是自不量力,不知天高地厚。
然而,我去意已决。临行前,我找到邓晓阳,满心不舍地对她说:“忘了我吧。”邓晓阳全然不顾这是在办公室,一把紧紧抱住我,斩钉截铁地说:“哪怕是上刀山、下火海,我也要跟着你。”我耐心地劝了她几句,我深知自己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,可不敢替心爱的晓阳做决定,未来的路充满未知,命运难以预测,我可以去冒险,但绝不能让她陪我一起陷入未知的险境。
第二天,我告别了父母,坐上了乡镇的公共汽车,准备先到省城,再转车前往魔都。车子缓缓驶过乡大院,我目光紧紧盯着那熟悉的建筑,却始终没有看到那个心心念念的身影。
当公共汽车即将驶出乡镇时,我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,满心的落寞与惆怅。不管愿不愿意放下,似乎都不得不放下了。就在这时,公共汽车突然被拦停,我抬眼望去,一个无比熟悉的面容出现在车门口,是邓晓阳!她手里提着行李,脚步匆匆地朝着我走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