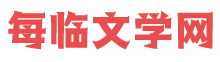《江米人》 第1章 霜降 在线阅读
在华北平原广大的农村,对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而言,日子是散漫而模糊的。太阳一天天升起来,又一天天落下去,每天的生活都极其相似,不需要刻意记得什么,也不需要刻意忘掉什么。但是,对曹南县邵安镇王楼村的江米人老艺人王清明来说,这又似乎是个例外。
农历丙申猴年,王清明已经七十一周岁了。俗话说,人生七十古来稀,近些年来,他常有一种人到暮年的危机感。而且,由于自认为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完成,因此特别珍惜这余生不多的时光,尽可能地去把生活打理得清晰而紧凑,使自己如同上紧了发条的钟摆一般,每天都不停地忙碌着,甚至巴不得要把一天掰成两天来用。可尽管如此,他现实中仍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,令自己常常生出一些无奈和叹息来,并在内心的某个角落,时不时泛出只有自己才懂得的忧伤。
在节气霜降过后立冬还未到来的这段日子里,鲁西南大地几场雨水过后,天气明显变冷了许多。黄河故道两岸的树木叶子渐黄,湿地的芦苇白花花一片,藕塘中也是一片残枝败叶的景象。于故道大堤上放眼望去,两岸的大豆、玉米等庄稼早已收获,原来以绿色基调为主的田地,现在裸露出黄褐色的胸膛。尽管少了许多往日的色彩,但在两岸的一些田地里,仍有一些红薯、白菜、大葱等未收获的植物,在经历风霜之后更显青翠了。而若留神细看的话,在已播种过的麦田里,一行行嫩黄的芽苗儿不知什么时候钻出了地面,这些小精灵们在地垄里整齐排列着,于冷风中抖擞着身姿,让人感到些许的希望和欣喜来。
往年这个时候,王清明大多准备好了家什,要出远门去卖江米人了。但今年的境况不同,除了老伴张桂芝因他上了年纪不同意他再出去外,家里家外不断发生的一些琐事儿,也弄得他很不安生,使他心里时不时地着急上火。
这天五更时分,王清明和老伴早早醒来了。窗外的天还黑着,他们在被窝里聊了会儿家事后才起床。王清明扫过了院子,对正要淘米做饭的老伴说:“他奶奶,恁做好了饭先吃,不要等我,俺去田地里转转。”然后,唤了在牲口圈旁卧着的那只通体黑色的老牙狗:“黑黑,过来啊伙计!”说着就要往外走,没走几步忽又停下,叮嘱老伴道:“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,金毛还在西屋,恁记得帮俺喂喂。”
黑黑是王清明收留的流浪狗,金毛是一位耍猴的老艺人送给他的猴子。俩畜生对王清明很是依赖,特别是黑黑,已经到了和他形影不离的地步,王清明走到哪里,它往往跟到哪里。
“他爷爷,吃过清早饭再去吧,俺正要去做嘞。”张桂芝已将淘好的小米下到锅里,边说边从馍筐里往箅子上拾要馏的蒸馍。
“我胃有些不得劲,清起来不想吃啦。”王清明回答。
“恁这多年的老毛病,不就是吃饭没个准点儿落下的!”张桂芝抱怨,“现在上了岁数,更不能饥一顿饱一顿啦。”
“我说了,不要等俺!”王清明不耐烦道,“做好了,恁就和真真娟娟俩丫头先吃。”
真真和娟娟,是老两口分别对孙女王真和外孙女朱娟的昵称。他们有一子一女,儿子王永福和儿媳李秀春,十年前就外出打工了,留下孙子王冬和孙女王真在家里。王冬比妹妹长八岁,三年前考上了省城工艺美术学院,而王真正在本村上小学五年级。女儿叫王永凤,和女婿朱孝明也去沿海打工了,小夫妇也有一女一子,女儿朱娟所在的村小学教学质量差,便把她放在了娘家,和表姐王真一起在王楼村的小学就读。儿子朱宾还小,由留在村里的爷爷奶奶照看着。
“地里都忙得差不多了,还去转啥?”张桂芝仍然唠叨着。此时她已将锅盖盖上,正准备在灶台点火,火柴划燃了,却又吹灭。
“我想去故道脚下的碎坡地,去看看那半亩大白菜。”王清明解释说,“霜降已过,说不定啥时候天就冷了,能捆就早捆了吧。”
——在华北地区的鲁西南一带,农户往往在立秋前后种植大白菜。大白菜的生长期短,气候适宜且水肥充足的话长得很快。霜降过后的天气不稳,往往有寒流发生,为不被冻坏和便于储存,大约收获前的半个月,要将散开的叶子进行捆绑。
“我的个老天爷嘞,人家都没捆,恁这是急啥嘞!再说捆早了,产量上不去不说,叶子嫩着也不好储存啊。”
“我有些等不及啦!”王清明说,“捆好白菜后,俺还有其他紧要的事嘞。”
“俺知道恁为啥急,不就是想早天出去卖江米人么!”张桂芝瞥了老伴一眼,“他爷爷,今门儿俺可要把话说在前头,恁就别打这个主意了!”又说:“儿女们打工前一再叮嘱,要俺管好恁,岁数大了就不要再出远门啦。”
“孩子们懂个啥!”王清明有些急躁道。说着从怀中取出白铜烟锅,在烟袋里压满烟叶,点着火吸了一口道:“甭听他们瞎叨叨,俺啥样自己能不知道!”
张桂芝来了气:“真是茅屎坑的石头又臭又硬,都这岁数了,还像年轻时一样别劲!”说着扬了扬手,对那黏着王清明的黑狗指桑骂槐道:“去,找金毛玩去,再不听话,看俺不打烂恁这拧劲头的脸!”
黑黑似乎并不害怕,竟然跑到了院门外,一副非出不可的样子,王清明吐了口烟雾呵呵道:“看,这畜生非要出去,我有啥法?”
“还说嘞,都是你给惯坏的!”张桂芝恨恨地瞥了老伴一眼,“一只狗让恁挝恁就挝,俺的话咋就不听嘞?”
看和老伴说不通,王清明不再理会,背着手出了庭院,和黑黑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。张桂芝紧追了几步,对王清明的背影喊:“外面冷,可别冻着!”看王清明没反应,又大了声说:“早点回来,俺和孩子们等恁回来……”
清早的王楼村很是安静,大街上空荡荡的,偶尔传来几声鸡叫或狗吠的声音,村庄仿佛一半醒来一半还在睡梦之中。路过村中央十字街的村委会时,王清明看到老支书王清河,正耷拉着脸披着马褂从村委大院出来。
王清明犹豫了一下问:“清河咋啦?夜里在大队睡啦?”
王清明所说的“大队”,现在应该叫“村委”或“村两委”的,是党员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的简称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基层政权组织推行人民公社化,下辖农村设“大队”,大队下面还设“队”或“小队”。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撤“社”建“乡”,“人民公社”改为“乡”或“镇”,各生产大队也陆续更名为“村民委员会”。但是,已经叫了几十年的称呼难以改口,像王清明这样土生土长的农村人,依然习惯称“村委”为“大队”。
王清河和王清明是近门子,论年龄比王清明长了几岁。今天清早,王清河有些不高兴,本不想多说话,看王清明对他招呼,还是呵呵着应了一句:“嗨,我是刚来这儿!”
王清明又问:“这么早来大队,有急事儿?”
王清河以前也吸烟,但后来得了气管炎便戒了。此时他咳嗽了几声道:“霜降已过,按理说秋收秋种的事儿忙活得差不多啦,可有些人家不像话,该种的不种,该收的不收,地就撂荒在那儿,俺想在大喇叭里再吆喝几声……”
在王楼村,王清河是说一不二的,村支书和村长一肩挑了几十年了。直到前年村委改革,上面要求“村两委”分开,他才不得不将村长给让了出来。不过,在他的操作下,村长由他最小的四儿子王永全接了。现在村里的许多年轻人要么去城里安家,要么到外地打工,要协调处理的村务事儿少了许多,可他对当村长的儿子不放心,有些事儿还得亲自去过问。
“可俺没听到喇叭响嘞?”王清明疑惑地问。说着,指了指自己的耳朵,自嘲道:“上了岁数,不好使啦。”
“不是恁没听见,是俺压根儿就没广播成!”王清河解释,“小四他昨晚不知干啥去了,夜里没回家,就睡在了大队里,门从里面锁死了,俺咋叫都叫不应嘞。”
“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,睡得晚起得也晚,不像咱们这些老家伙,不管头天睡得多晚,第二天准得按时醒。”
“说得对嘞,特别是心里有事儿,更是半夜半夜的合不上眼。”王清河说,“咱们村这几年,乱七杂八的事儿不少,俺一想起来就睡不着啊!”
“我说句话,清河恁别往心里去,恁家永全当了村长,就放手给他干好了,你别再管那么多,有时间就去享享清闲吧!”
“唉,俺也盼着能这样。”王清河叹息道,“小四和恁家永福同岁,恁是知道他的,这小子爱玩,村里的事儿没放在心上,俺怕一撒手就乱了套嘞。”
离开王清河,王清明到了十字街东南角的一口老井旁,老井旁有棵老槐树,他靠近了,扶着黑褐色苍老的树干站了会儿。
这口老井,据说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井水虽然有些苦涩,却曾是全村老百姓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。男人们常从这口井挑水做饭、饮牲口,女人们也常在井旁淘米、洗衣服,大家相见了,往往拉拉家常,戏耍说笑几句。直到后来全村通了自来水,井旁才渐渐冷清下来。水井旁的这棵老槐树很粗,四五个成年人才能勉强搂抱过来。树干虽已中空,生命力却极其旺盛,每年都会发出新叶抽出新枝,开出黄灿灿的槐米花,结出饱满的果实来。
古代先民们生产力低下,为了生存便逐水而居。曹南县境内古有黄河、济水等大河流经,更有汜水、汳水和蒙泽等大大小小的古河流湖泊,为先民们提供庇护和保障。据考证和资料记载,龙池地区的曹南县历史极其古老,曾为黄帝、尧、舜之都居,也曾是鲧、禹受尧、舜之命治理洪水之地。
曹南县境内原有曹南山,夏禹母族有莘部落就位于曹南山附近。夏禹父亲鲧娶有莘氏女生夏禹,后夏禹又娶曹南县境内涂山氏女为妻生启。夏禹治水成功后在曹南县称帝,后传位于子启,改禅让制为世袭制,开创中国近四千年家天下之先河。商成汤灭夏后,初都城也在曹南县,只是后来因黄河水患才不得不将都城西迁。也正是这个原因,曹南县被史学家称为“商汤开国地”和“华夏第一都”之所。
这一带曾出过众多的名人志士,如商朝开国宰相伊尹、商纣王叔父后东去朝鲜建立王朝的箕子、思想家文学家和道家学派的奠基人之一的庄周、战国名将吴起、西汉农学家氾胜之、隋末唐初猛将单雄信、唐末农民起义首领黄巢、北宋科学家画家燕肃,等等。之后历史中也是名人辈出,就近现代艺术界而言,豫剧五大名旦中,就出现了马金凤、崔兰田等两位大师级人物。
关于王楼村村庄的历史,口口相传说法不一。从一些遗址和传说来看,这一带至少已有几千年了,只可惜后来黄河多次泛滥,原来的遗址多深埋于黄沙之下。从王氏家谱记载来看,现在王楼村的王姓人家,系元朝一户做高官的王姓先人,在家道败落后,其子弟几经辗转,最终认定王楼村这块风水宝地,在此开荒种地繁衍生息。经过几十代人的不断努力,村庄的人口越来越多,规模也越来越大。后来虽有其他姓氏迁入,但王姓仍是村中绝对的大姓,在方圆一带一提起王楼村,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
王楼村建于被称为“堌堆”的一片古高地之上,东西狭长。东西街南侧,对称分布着两个很大的池塘,村民们分别称之为“东大坑”和“西大坑”。据说王楼村四周原先是有寨墙的,修筑这些寨墙的土多取之于两个大坑。后来村庄一步步扩大,寨内再也容不下越来越多的村民,又因为和平年代没有了战争和匪患,寨墙无存在下去的必要,后来便被拆除了。
村里有条十字街,将村庄大致分成四部分,每个部分被划成一个小队。东街靠北部分的为生产一队,以此为基准,顺时针分别为生产二队、生产三队和生产四队。每个生产小队各设正副队长一名,都在村大队两委的领导下,组织生产劳动并开展其他村务活动。大队支书王清河家在生产一队,队长由任村长的王永全兼任。王清明家在生产二队,队长也是一位王姓本家,可自从这位本家半身不遂后,副队长李根便接过了这个担子。三队队长是焗匠唐付忠,副队长是老铁匠的儿子,外号“二铁匠”,叫仝宝库,两人以前不经常在家,管理基本上处于相对涣散的状态。四队中武姓人家占多数,队长是木匠武凤轩,副队长是村会计黄学文的父亲黄二蔫,可自从黄二蔫去年得癌症去世后,队里的大小事务实际上由武木匠一个人来操持。
东西街是王楼村的主干道。街道出村后向西延伸,与去往其他乡村的道路相通。向东出村后再走一华里左右,与南北向的一条省道相连。这条省道向南通达邻省,向北可到达邵安镇、曹南县县城和龙池地区首府所在地。村庄的四周有四条相连的道路,道路内侧是相互贯通的小河。村十字街往村外延伸的道路,与四周的小河交汇,分别各有一座小桥。这些绕村的小河道与村里的两个大坑相连,向外又与两条南北走向的大河互通。村外的这两条大河,又相接于故道大堤的水库河塘。这些贯连互通的水网,旱时能用来灌溉,涝时能用来排水,对防患水旱灾害往往能起到积极作用。村里的十字街又与多条胡同相连,四通八达,鸡犬之声相闻,站在街头喊一嗓子,半个街道都可以听到。
在老井旁待了片刻,王清明顺着南街出了村。过了村前的小桥,沿着绕村道路向东走去,接着又拐向南北向道路。此时大地上缥缈着雾气,东方的天空虽然比刚才明亮了一些,却仍看不到太阳。
快到村东头的小河桥时,王清明在雾气中隐约看到,王清田和陶行善两人,正在桥头讨论着什么——俩人似乎谈论得很认真,也很激动,双手比划着,指指点点,身子随着说话一倾一仰的。
王清田是支书王清河的亲堂兄,曾任本村小学的校长,现退休闲居在家。陶行善是本村赤脚土郎中,从父辈手中接过中药铺子“百济堂”,近些年尽管吃药打针的人越来越少,但仍然惨淡经营着。两人和王清明差不多同龄,几个人的关系很好,遇到一起无话不谈。
在王清明看到对方之前,王清田和陶行善已经发现他了。发现他并不是因为看到了他本人,而是先看到了他的那条大黑狗——当时黑黑跟着他在路上走着,突然前方出现了一只偷鸡的黄鼠狼,黑黑发现后扑了上去,黄鼠狼丢掉母鸡后便逃,黑黑便往前追,谁知黄鼠狼有些戏耍黑黑似的,在前面时紧时慢地跑,并不时回头嘲弄黑黑。黑黑愤怒,愈发卖力地去追。快追到小桥头时,黄鼠狼看到王清田和陶行善,一转身下到小河里,并在桥下很快不见了。黑黑空手而归,气得不停地扒着爪子,“呼哧呼哧”地直喘粗气……
看到黑黑,王清田惊讶道:“这不是清明家的狗么?咋跑到了这里!”
陶行善说:“黑黑是清明的跟脚狗,可能清明就在附近嘞。”
正说着,王清明来到了跟前。王清田笑呵呵道:“清明啊,正说恁嘞,说曹操曹操就到了。”
黑黑看到主人,沮丧地耷拉着脑袋。王清明嘲讽道:“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,看看,丢人现眼了吧。”
陶行善笑道:“清明恁也不要挖苦黑黑,狗和人一个样,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啊!”
王清田和陶行善不吸烟,王清明也不让他们,自己掏出烟布袋挖了锅烟叶点上火,吸了一口道:“行善说得也是,狗的寿命只有十六七岁,黑黑跟俺也有十来年了,是显老了啊。”
“又到了收起了,今年还出去卖江米人么?”王清田换了一个话题,“以往这个时候,恁可大都要出远门的。”
“收起了”是鲁西南一带的土话,大致指每年深秋庄稼收完入仓地里的小麦也种完之后,直到春节前后的这一段农闲时节。
鲁西南方言很有自己的特色,曹南县位于苏鲁豫皖交界处,语言更富有特点。这一带的语言属于北方方言中原官话的一种,和豫东方言较为接近。突出的特点是没有翘舌音,而且基本音调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可以有新的音调。例如在当地“说”读“fo”,“叔”读“fu”,“喝水”说“喝fei”,“吃药”说“吃yue”,“红薯”说“红fu”。这一带的方言中,也有很多古语词的遗留现象,多体现于当地一些特殊的民俗词语中,如称谓“你”用“恁”,“我”用“俺”,“我们”用“咱”或“咱们”,母亲叫“娘”,父亲叫“大”或“大大”,儿子叫“小”或“小来”,女儿叫“妮”或“妮来”,姑姑在当地不叫“姑姑”叫“嬷嬷”;对一些自然事物的称谓也很特别,如说“太阳”为“天亮地”,说“夜里”为“黑家”,“脖子”叫“脖拉梗”,“膝盖”叫“格拉拜子”,等等。这一带方言中的词缀也极具特色,如名词词缀主要有“子”“头”等,如粪筐说“粪箕子”,发霉说“长醭子”等;而“头”多指人,且多含有贬义,如说坏人为“败坏头”,说倔强的人为“拧劲头”。另外,这一带还有其他众多的土话口语,如“可以”说“管”或“中”,“舒适”说“得劲儿”,“生病”说“不大得”,等等。
“正合计着嘞,”王清明回答王清田说,“现在手头还忙,等把一些活计忙完了就出去。”
“不愁吃不愁穿的,还跑出去干啥。”王清田呵呵道,“虽然你比我和行善小了两岁,可也过了七十了,身体要紧嘞!”
陶行善也说:“是啊,清明的身体的确不如以前啦,光今年,就到我家的铺子拿过几次药了!”
正说着,四队队长武凤轩顺街而来。他骑着一辆老旧自行车,后座上载着一个老旧的木箱,左边挂着一大一小两把老旧的木锯,右边则挂着一只老旧的锛铲——锯和锛这些工具较大,木箱里盛不下,就挂在了自行车后座的两边。那个老旧木箱王清明熟悉,里面盛着斧子、凿子、刨子、钻子以及墨斗、尺子之类的木工用具。
王清田问:“凤轩,看这架势,又要去干木匠活?”
武凤轩上面几代人都做木匠。他继承了家传,在村西头开了个木工作坊,平时接些本村和附近村庄的木工活,也有时下乡招揽生意。听到王清田招呼,武木匠回道:“地里收拾得差不多啦,在家闲着也是闲着,趁机出去治几个。”
“是遛乡还是去固定的地方?”陶行善也问。
“遛乡!本来是有固定场所的,可俺给推了。”武木匠说。又解释道:“干泥水活的葛存礼捎话来,说镇建筑公司需要木工,问我去不?可俺想自由单干,不愿听人吆三喝四的,便没答应。”
一提起葛存礼,王清田忽然想起了什么,急切地问:“葛存礼在工程队忙不忙?我和行善正要找他嘞。”
葛存礼是王清明的干儿子。小时候,他跟生产队喂牛的瞎二爷玩,不小心被瞎二爷的鞭梢子打到了眼上,一只眼睛出现了玻璃体,白眼珠多黑眼珠少,看东西也模糊,从此也有了个“白拉眼”的外号。父亲葛老三和母亲吴凤英没大本事,有个上学的弟弟葛存义还要花钱,家里穷得经常揭不开锅。为了生计,十五岁那年经人介绍,便跟了邻村一位包工头干起了泥水活。他先从做小工掂泥兜子开始,后来掂了瓦刀成了大老师,目前已是工程队不可多得的“泥瓦匠”好手了。然而,他性格过于内向,平时憨实得像个傻子,一天说不上几句话,特别是眼睛受损后又多少有些自卑,再加上家景过得太穷酸,以至四十好几了还没成个家。虽然他自己并不怎么在乎,可父母却愁得睡不好觉吃不好饭。王清明夫妇也很关心这位干儿子的私事儿,托关系说媒为他介绍了几个女人,甚至还介绍过附近村庄的寡妇,可对方知道他的情况后便都拒绝了。
葛家在四队,作为队长的武木匠多了解他家的情况。武木匠回答王清田说:“存礼忙得很嘞,这小子平时不说话,心里却啥都明白,为能给家里挣些补贴,干起活来不要命,几乎是天不明就离家,天黑了才回来,有时还吃住在工地上。”说过,又疑惑地问:“你们找存礼干啥?”
“干啥?还不是他是泥瓦匠,想请他把这村头的小桥给帮着修了。”王清田解释道。说着指着面前的小桥道:“这桥虽小,却是出村到镇上和去县城的必经之路,现在坏得不成了样子,没了栏杆不说,桥面也出现了缝隙,车轱辘经常陷进去。”说到这里,又望着王清明说:“今年麦收时,你家的那头叫驴,不就是在这儿把腿给崴断了?还有年长的五奶奶,去年也是在这儿摔了一次,脚肿得老高,一个多月不能走路……要是再不修,恐怕还会发生大事故!”
王清明说:“是啊,这桥早该修了。俺因这事还找过村委,可清河支书说,修是该修,可就是愁没钱嘞。”
陶行善也说:“这事儿我也知道一些,今年春上俺给清河治气管炎时,听他说曾给镇上打了报告,想从上面争取资金,可一来二去,却没了回音。”
王清田说:“虽然我和清河是叔伯兄弟,他又是支书,背后不应说他的不是,但大家谁不知道他?别看表面喳喳乎乎,心壳朗小得很,难讲话不说,还办事武断,好摆治人,他不同意的事儿,恐怕很难办成嘞。”
“不仅清河难说话,他当村长的儿子更不值供,若得罪了他,非得掐给你亏吃不可。”急脾气的武木匠也愤愤道,“既然他们爷俩不愿啰啰,咱们就自己干!把全村四个小队动员起来,能出钱的出钱,想出人的出人,俺就不信,没有大队这桥就修不起来?!”
“自己干管是管,以前村里的有些事儿,没有村委不也一样干了么!”王清田想了想说,“可毕竟修桥不是小事儿,再说这桥还在村村通的公路上,俺的想法,为了稳妥起见,不管清河问不问这事儿,都得给他说声,若绕过了大队,怕日后生啥幺蛾子。”
陶行善也说:“清田说得在理,大家不要急,心急吃不到热豆腐嘛!”又说,“清田气管不好,我过几天给他看病时,好好给他讲讲,看他究竟啥想法……”
前些年,作为贫困县的曹南县,大力响应上级提出的公路“村村通”号召,积极争取资金加大基础设施建设。邵安镇利用这次春风,将几十个自然村之间的路连接了起来,并将路面给硬化了,主要路段修成了水泥路或者铺了柏油。
王楼村邻近黄河故道,河网纵横,修路条件较为复杂。与该村真正相连的被硬化了的公路,只有贯穿全村东西街的这一条。南北街虽然村中的这段是条水泥路,但出了村还是土路。土路延伸出到村前村后的田野——王楼村四面都是田地,这条延伸出去的南北乡间小道,在经过多次的人走车轧之后,路面有些坑坑洼洼,旱季常扬起尘土,雨天又多显泥泞。
刚才于村东头小桥处,几个老汉议论了一番要尽快修桥的事儿。王清明心里想着要去看大白菜,没说几句便离开了。不久,他绕到村后的小道上,刚要拐弯时,遇到了二队副队长李根。此时李根正开着机动三轮车,要去龙王庙附近的田地里收红薯。
王清明和李根两家同一个胡同。李根的父亲李保银比王清明长几岁,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也最好。李保银父母死得早,家庭条件又极差,一直没能说上媳妇。到了不惑之年时,才在五奶奶的张罗下,收养了一个同样父母早亡的流浪儿做义子。老汉很疼爱这个孩子,为他取名李根,从此算是有了接续香火的人。李根长大后该成家了,可当地人嫌他穷,光棍家庭的名声也不好,没有哪家的姑娘愿意嫁过来,李保银为此愁白了头。后来,在王清明等好心邻居的帮助下,才多方筹集了钱款,又卖了头喂养的牛后,才从被叫作“人贩子”的那儿,给李根买进家一个叫“山茶”的女人。
山茶来自南方山区的少数民族,不懂鲁西南当地风俗,王楼村的一些人对她好奇,背后对她指指点点。更重要的是,李家太穷了,山茶开始感到失望,便有逃走的想法,并且实施了几次,但都没成功。后来,对丈夫李根有了一定了解,和老实能干的李根也渐渐有了感情,想逃离的想法便渐渐打消。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,更是铁了心和李根过起了日子。山茶为李家生养了两儿一女,最大的是女儿,叫春草,今年九岁。第二个是男孩,叫狗蛋,刚满七岁。最小的也是个男孩儿,叫猫蛋,才刚刚三岁。猫蛋什么都不懂,还经常赖在妈妈的怀里吃奶。李根憨实,家里地多,孩子又小,另外还是有些担心山茶跑了,所以就没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外出去打工……
几十年前还在大集体时,当时还年轻的保银老汉就给生产队喂牛。多年来,他摸索出一套很实用的喂牲口的经验。现在,他家除喂有鸡鸭鹅等家禽外,还喂养了一大一小两头黄牛、一头母猪和几十只绵羊和山羊。原先,他家的牛和羊并没有这么多,去年,上面推行精准扶贫活动,发放了救助款,他家又自贴了些钱款,买了两头牛犊和几只品种好的母羊。后来,牛犊慢慢长成大牛,母猪已下了两窝崽,绵羊和山羊也繁殖很快,已由十几只增长到几十只了。家里的牲口多了,保银父子俩常为饲料的事儿而担忧。
李王两家离得近,多年来,王清明每年都要外出去卖江米人,张桂芝一个女人在家里难以顾得来,有困难了便常找李家来帮忙。后来,王清明夫妇年纪大了,儿女们又不在身边,除了黄河故道大堤下不多的碎坡地还是自家来打理外,主要的大田地便交由李家来耕种。两家已经约定好,李家帮着耕种土地,每年的粮食收成,除了按一定比例交给王家外,所有田地的秸秆,要由李家来收获,以用来弥补牲口饲料的不足。
看到王清明,李根停下了车子,问:“叔,恁这是干啥去嘞?”
王清明指了指远处说:“去看看大白菜,要是能捆,就尽早捆了。”
这事儿甭急,晚几天俺帮恁来弄吧!”李根诚恳道,“这段时间俺忙,恁家的活没顾得上。”说着,也指了指故道大堤的方向道,“咱两家的地里,还有些棒子秸和棉柴没能收回家,俺正想着处理嘞。”
“恁先忙恁的,小块地的这些白菜萝卜,我和恁婶儿就能干。”王清明解释,“根儿,收红薯时,给俺留些红薯秧,俺捆大白菜用。”
“叔恁就䞍好吧!”李根说着,发动起三轮车。跑了十几米后又回头说:“叔,俺想明年包地种,恁家的田地如果不想种了,都转给俺好了,恁回去和俺婶子思量思量。”
王清明顺口“哦”了一声,便不再言语。望着李根的背影,一边思考着他刚才的话,一边慢悠悠地继续往前走。黑黑毕竟是畜生,此时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沮丧,瞅瞅这,嗅嗅那,并时不时地追逐路旁和田野里的小动物,王清明也不管它。
十字街往北的这条小道,从村后直通黄河故道大堤。小道靠左的位置,有处不知什么年代形成的堌堆。堌堆两三米高,四四方方,有足球场那么大。上面有处废弃的不知啥年代的龙王庙,只剩下周围十几棵柏树和一些残垣断壁,到处长满了杂草。周围有几处坟地,村民们对这一地方感到畏怯,除了耕种收获劳动外,平时很少有人来这里。直到去年,政府要搞精准扶贫,村委在龙王庙的废墟上建了两套安置房,将在故道河滩里居住多年的阴阳先生蒋荣水,以及他外号“四拐”的徒弟王永民,给一起搬迁了过来。
快到龙王庙时,隐隐约约看到蒋荣水从新宅子里走了出来,后面跟着徒弟 “四拐”。两人的肩上,都搭着一个鼓囊囊的灰褐色的布包,看样子要出门。
看到王清明,蒋荣水和四拐迎了过来。待王清明走近了,四拐抽出香烟递给师傅,又递与王清明一支。王清明摆了摆手:“你这个没劲,俺吸自个的。”说着从怀中抽出了白铜烟锅。
王清明吸着烟,问蒋荣水师徒:“新房住得还中吗?你们搬来后,俺还没来看望过呢。”
没等蒋老汉回答,四拐抢先道:“中是中,可俺们心克朗子再大,也怕……”说着望了师傅一眼,欲言又止。
王清明疑惑:“毕竟是新房,总比在河滩里住强吧!”
“唉,一言难尽啊!”蒋荣水叹息,“这里曾是龙王庙,俺们搬来后,时常遇见不干净的东西,睡觉也常做噩梦嘞。”
王清明“嗯”了一声没再言语,眉头却紧皱起来。猛吸了几口烟,转移话题问:“看你们这样子,是要出门?”
“我和四拐要去故道北的赵河村,”蒋荣水道,“这村有户人家的老人快不行了,要请俺去点个坟……”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农村改革实行包产到户,王清明家分了十几亩田地,有大块地也有碎坡地。大块地主要种植玉米和冬小麦,耕作方式主要靠牲口和机械。小块地较零碎,而且不规整,耕作主要靠人力。这样的小块地又分为两部分,一部分位于村南,那儿有口机井便于浇灌,主要根据季节的不同种些适宜的蔬菜,如春天种些香菜油菜,夏季种些黄瓜豆角,秋后则种些大葱撒些菠菜之类。这儿离村子较近,采摘也方便,平时家里吃的菜,基本靠这片菜地来解决。另一部分,则位于故道大堤脚下,这儿地势不平,河道池塘较多,主要在春夏季节点种些玉米、绿豆、芝麻、高粱之类,立了秋后也会撒些萝卜,种些白菜等。特别是大白菜,这可是一家人过冬的主要蔬菜。今年立秋前后,王清明老两口又在这里种了大白菜。儿女们都外出打工了,老伴一个女人家又上了年岁,王清明担心她忙活不过来,便想在外出卖江米人之前,将能收拾的尽量收拾了。这段时间以来,他里里外外忙活得不可开交,现在还剩下多半亩大白菜没有收。
王清明离开蒋荣水师徒后,继续朝前走,很快便来到了大堤下,并径直去了自家的白菜地。大白菜长势不错,一排排绿油油、水灵灵的,而且大都包起了心,如果再将外面的叶子捆起来,肯定是个好收成。尽管捆白菜的时间早了几天,可急于外出的他有些等不得了。按他的想法,先将白菜捆起来,立了冬由李根帮着来收获。
出了白菜地,王清明带着黑黑上了故道大堤。此时天已大亮,初升的太阳有些害羞似的,绯红着脸蛋,在雾气和云层中时隐时现,远处的王楼村,如一幅灵动的水墨画。不知谁家的烟囱里,袅袅地升腾起了炊烟,并在空中变幻着各种形状,又慢慢地飘散开来,而随着雾气在微风中淡淡飘流,村庄似乎动了起来,乍看仿佛一条蠕动的卧龙,在雾气中慢慢游弋着身躯。
到过王楼村的人都说,王楼村建村时肯定经高人看过风水,并且按指点进行了规划。如果置身于村中还不能看出奥妙的话,那么从故道大堤上俯视就会惊讶地发现,东西狭长的王楼村仿佛真是一条盘着的卧龙,贯穿东西南北的十字街是龙脊,排列整齐的上百家农户是龙鳞,而村东和村西对称分布的两个大坑则是龙的眼睛。龙离不开水,王楼村的大河与小河相交,纵横交结,把村庄置于河网之中。而这条龙又傍依在黄河故道这条巨龙身旁,一大一小横亘着,汲取着营养,同时又守护着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。
关于这一点,村里的老人口口相传说,先人们在村落的选择和修建上,的确经过了高人指点,并且进行了缜密设计和规划。村里村外这四通八达的水网,主要功能是旱时引水浇灌,涝时疏通排浚,另外也能起到消防之用。村里的麦秸垛和个别人家失过多次火,正是这些大坑和河道里的水,为灭火起了关键作用……
故道大堤上,王清明一边观赏风景一边胡思乱想着,此时远方传来了几声李保银老汉的呼唤:“哎,清明……哎,清明……过来吸袋烟嘞……”
循声看去,果然是保银老汉,正赶着羊群从一条河沟里向这里慢悠悠而来,后面还跟着他家那只叫“黄妮”的通体黄色的母狗。
——老实巴交的保银老汉,平时除帮儿子李根干些农活外,就是专心放他的这群羊。他放羊的地点,多在黄河故道的大堤附近,有时是在大堤之上或大堤两侧,有时是在附近的河沟或田间地头——这些地点不便种植庄稼,野草和灌木却长势茂盛,能给羊群提供丰盛的食物。现在,老汉不停地甩着鞭子,顺着河道将羊群赶上了大堤。看到王清明后,把羊群圈在灌丛中吃草,并对他家那只母狗说:“黄妮,帮俺看好这群羊,特别要看好那只领头的骚虎头,俺过去和清明说会儿话。”
黄妮仿佛听懂了主人,在羊群周围来回跑了几圈,接着蹲在了那只骚虎头旁。但老汉似乎仍然不放心,没走几步又回头叮嘱:“我不在时可不能偷懒啊,如果有羊偷吃了庄稼,看不敲断恁的腿。”黄妮朝老汉汪汪地叫了几声,似乎在说:“放心吧,主人,我会尽责的。”
此时的王清明也迎面走来,黑黑看到黄妮很是兴奋,没等主人吩咐,早已跑到前面去了,王清明嘿嘿地笑了两声,骂道:“这畜生,还像年轻时那样骚情!”
两人越走越近,快到跟前时,李保银掏出烟袋锅要装烟叶,却发现烟袋瘪了,遗憾地自嘲:“看我这脑瓜子,晕头呱叽的,咋出门就给忘了呢?”王清明见状,忙递过自己的烟袋说:“吸这个……不久前从集上买的,味道不错嘞!”
保银老汉也不客气,在王清明的烟叶袋里挖了一锅,边挖边解释说:“我成年累月地不外出,烟叶都是根儿去镇上时给俺捎买的,可这段时间地里忙,根儿也没能出去。”说着将挖出的一锅烟点上火,吸了一口,啧啧称叹道:“好,好,吸着带劲嘞!”
王清明也挖了锅烟叶,使劲压了压,点上火吸了一口,吐着烟雾道:“刚才来到路上,我见到恁家根儿了,他说要去地里刨红薯。”
“这俺知道,他已刨了两天了……地里还有一些活,譬如恁家的玉米秸、棉柴,还没顾得上往家拉……原本想使它们再在地里干透了,等把红薯、胡萝卜等地里剩下的作物收了后,再去弄那些。”
“甭急,在地里再干干水分也好,反正该收的果实都收了,只剩下了秸秆,早天晚天不要紧。”
保银老汉没再继续这个话题,而是问:“往年这个时候,恁差不离儿该出去卖江米人了吧!”吸了口烟又说:“俺知道,永福他娘和孩子们都认为恁年纪大了,不想让恁再出去,可依恁的脾气,不出去又哪管!”
“还是恁懂俺!”王清明感慨,“我早就打算好了,今年还要出去的,只是,手头还有些事儿要收拾。”
“永福他娘和孩子们想得也对,恁毕竟上了年纪,能不出去还是不出去的好,”李保银劝道,“再说,人终归会老的,无论干啥,也总有搁手的那天。”
“除了江米人,我没其他喜好乐趣,不出去会憋出病来的……”
两人这样说着时,保银老汉家的羊群在那只骚虎头的带领下,跑到堤下的麦田里,贪婪地啃食起了刚露出地皮的嫩苗来,而看护羊群的那只黄狗,不知什么时候没了踪影,而且黑黑也不见了。
“黄妮这个骚货,见不得牙狗,又和黑黑搞起来了吧。”保银老汉骂道。
王清明呵呵道:“我家黑黑也是,都是条老狗了,还和年轻时那样,见了母狗就兴奋!”
“清明恁去吧,我要照顾这群畜生!”保银老汉说着就要离开,边急着跑下大堤边道,“出门前和我说声,俺想再和恁喝气嘞!”没走几步又回头说:“恁家没有忙完的活,由我和俺家根儿来干!”
正说着,黑黑跑了回来,又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。王清明骂道:“我说过多次了,啥年纪要做啥年纪的事儿,毕竟老了嘛!”
黑黑似乎并不服气,呜呜地叫了几声。这时,前方灌木中出现了几只野鸡,一边悠闲地迈着步子,一边觅食着草丛里的种子。黑黑冲了上去,受到惊吓的野鸡扑拉拉飞了起来,却又在不远处的草丛中落下。黑黑又去追,野鸡再次飞起,不过这次却没有落下,而是朝别处飞远了。黑黑喘着气,再次耷拉着头回来。
“黑黑孬种了吧!”王清明再次嘲讽道,“我早就说过,恁不是年轻那时候了!”
黑黑摇了摇头,呜呜了几声,似乎在说:“还说俺呢,难道恁不和俺一样儿!”
下了大堤,王清明按原路返回。此时的太阳冲出了云层,金黄的阳光照耀着大地,也照着王清明和黑黑。望着有些萧瑟却广阔的田野,王清明感到心胸舒朗了许多,不由得长长地舒了口气,正想哼唱几声什么时,忽然不远处的河道旁传来说唱坠子书的声音,声调高亢,是名曲《刘公案》的前缀:
弦子一拉看三书啊,真听嘞那剩书开正封
这部书有心俺打头上唱,啥时候能唱到热闹中
这部书有心俺打尾上论,书到临尾渐渐松
掐了头来去了尾,俺要热闹三关唱当中
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