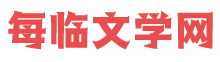《江米人》 第3章 奔丧 在线阅读
曹南县历史悠久,据考证,这里自夏朝末年就已出现了城市文明。三千多年来,这块大地上曾先后出现过如亳城、蒙城、己氏城、楚丘城、济阴城等大大小小十几个故城。元朝时,在楚丘县和曹州县之间建磐石镇。明朝初年,以磐石镇为基础兴建了曹州城,这就是后来的曹南县古城。明正统十一年,建竣后的县城设有四座城门,东西南北分别为望岳门、镇川门、阜民门和迎恩门。之后的继任者们又多次修缮扩建,加固了城墙,建设了城楼。为防水灾匪患,还修建了护城堤,开挖了护城河,将城墙由土墙改为砖墙,在四关增建了敌楼。1945年9月冀鲁豫部队和地方武装,在攻克县城后将城墙拆除。次年9月军队进驻后虽修整了城垣,但仅过几月后的1947年1月,解放军三野一纵一旅攻克县城后,又将城墙给拆除了。
对邻近县城的东西南北区域,曹南县人习惯称之为东关、西关、南关和北关。以前的古城墙虽然已被拆除,但以四个关命名的街道社区却保留了下来,王清明干娘五奶奶和妻子张桂芝娘家所在的村庄,就属于南关街道。
在兄妹六人中,张桂芝排行最小。她的命苦,母亲生下她后就死掉了,十几岁时父亲也不幸离世。长兄如父,当时大哥已成家,是大哥大嫂给了她呵护,并把她抚养成人。大哥是当地有名的“劁猪匠”,“劁猪”当地又叫“骟猪”。以前农村几乎家家养猪、养羊,主家为了猪羊生长得好,等公猪公羊长到一定月份,要把产生精子的睾丸给割掉,这就叫“劁猪”“劁羊”。张桂芝大哥会“劁猪”的手艺,不过这门手艺路子窄,后来大哥又学会了杀猪。按照当地风俗,杀猪的人猪肉归主家,猪下水却是由杀猪的人拿走的。后来养猪杀猪的少了,大哥又在邻近县城的路口,设摊卖起了猪肉。
大哥的生意虽然不大,但养活一个家还是绰绰有余。张桂芝跟着大哥一家,并没有受过多少苦。实际上,她不仅没有受过缺衣少穿的苦,哥嫂还特别疼爱她,处处让着她,不让她受一点儿委屈。当然,这样也造成了她较为任性和倔强的性格,给后来她的婚配之路带来了曲折,也因此落下了不好的名声。后来在五奶奶的牵线下,她嫁给了偏远乡村会捏江米人的王清明。尽管王楼村离娘家较远,丈夫王清明又经常外出,而且照顾孩子忙活里里外外的家务,但她很疼大哥,经常回娘家去看望。后来虽然上了年纪,腿脚不像以前那样灵便了,却仍坚持着每年都要回上几趟娘家。特别是近些年来大哥身体有病后,她回娘家的次数更是勤了。
刚才晚饭时,娘家大嫂打来了电话。大嫂对她说,这段时间天一冷,大哥的病又犯了,去医院治疗了半月不见好转,傍晚病情急剧恶化,医院通知家属准备后事,估计撑不了几天了,现在已从医院回了家。张桂芝听后惊愕不已,禁不住悲伤起来。
王清明安慰她:“大哥虽然病危,可毕竟还在世,恁这样哭哭啼啼的不好,咱明天看望就是了。”
“啥?明天去看望,可俺现在就要去!”张桂芝激动道,“我有种预感,大哥这次凶多吉少,能早见一面就早一点见。”
“咱这一带的风俗,过了午后看病人不吉利。”王清明道。
“人都病成了这样,还在乎这规矩那规矩!”张桂芝着急,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。
“你不计较,恁娘家人不一定不计较!”王清明解释说,“想想看,大哥到了这个关头,一旦有个不测,如果恁在不合适的时机去了,就不怕被娘家人埋怨。”
王清明说得在理,张桂芝也不好再说什么。心情渐渐平静下来,便和王清明合计,决定明天一早买了礼物再去娘家。然而第二天一早,还没来得及出发,娘家人就派人报丧来了,说大哥当夜三更咽了气,停丧五天后出殡。
尽管早有预感,报丧还是令王清明心头一震,愣在那儿好久没有说话,回过神来长叹一声:“唉……真可惜,当地最好也是最后一位劁猪匠走了啊!”。
得到噩耗,张桂芝差点背过气去。她先是捶胸顿足大哭了一番,接着便抱怨起王清明来:“都是你出的馊主意,正是听了恁的混账话,俺才没能见上大哥最后一面……”
“事已如此,再埋怨有啥用?”王清明劝说,“作为至亲,咱们目前要考虑的是如何吊孝随礼,帮助恁娘家人把丧事办好。”
“别光站着说话不腰疼,要具体说说咋办呢?”张桂芝急躁道,“大哥生前对咱家不薄,要知恩图报,把他的后事操设得像个样啊。”
“是啊,恁是大哥从小带大的,咱是应该好好表示的。可话说回来,你上面还有两个姐两个哥,二哥三哥咱就不比了,可总得和大姐二姐商量一下吧。”王清明说着,摸出烟锅装上烟叶点着吸了。吸了两口,又进一步解释:“按常理,咱们对照两个姐家随份就行了,可如果这样做,又显不出恁这个小妹的特别来……”
“我想好了,咱是不能跟俩姐家一样,”张桂芝打断王清明说,“不管她们咋办,咱都要给大哥扎个纸活,还要请个‘响’!”
张桂芝所说的请“响”,就是在出殡的那一天,要请个吹喇叭唢呐的“吹唱班”。办丧事请“吹唱班”,这是鲁西南多年来的习俗。唢呐所吹出来的喇叭声,在丧事上是一种情感的表达,也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如果谁家的丧事上没有“吹唱班”,往往被认为是种缺憾,甚至被视为不孝的表现。
没等张桂芝说完,王清明马上摇头:“不中不中,扎纸活和请‘响’的事儿,按说应该由恁侄儿侄女来办,扎纸活的事儿还好说,可请‘响’这事儿是大事儿,咱要强行办了,你大哥家孩子们的脸面往哪搁?再说,附近几家有名的吹唱班,后继无人大都自行解散了,现在镇上只有一家姜姓吹响班了,也不知他们是否接了活到时得闲不得闲?”说到这儿,王清明犹豫了一阵,又接着道:“俺的意见,扎纸活的事儿咱来办,可用不用‘响’,用啥样的‘响’,这个‘响’由谁来请,都得和恁娘家人商议后才行……”
“不要再说了,这事儿俺已决定!”张桂芝武断道。说着望了老伴一眼,又以不容置辩的口吻道:“还有,忙丧事这几天,恁得陪俺在娘家靠着,外面哪里也能去。”
对这个问题,王清明没有再说别的。然而他清楚,张桂芝说得容易,可真要按她的来办,确实需要很多的事要做。比如请吹唱班的事儿,请来请不来另说,但说费用一块就够人头痛的,因为一个吹唱班,吹笙吹唢呐和敲锣的在内,至少也得四个人,一天的费用可不是小数目。实际上,王清明的担心是有道理的,他虽然默认了老伴的决定,可经历太多人情世故的他,担心花费是小事儿,他还忧虑更多的相关问题——张桂芝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,按理说,娘家大哥去世,丧事如何办应由他们说了算,作为嫁出去的妹妹是不需要出头露面的。而且按当地的规矩,亲姐妹随礼应一个样,如果妹妹随得多而姐姐却拿不出同样的数目,姐姐们肯定有意见。还有,扎纸活请吹唱班,得由大哥家的亲闺女亲儿子来操办,张桂芝这个当嬷嬷的出头承担,侄子侄女们可能会没面子……
想到这儿,尽管知道张桂芝听了后会不高兴,可王清明还是将自己的忧虑说了出来。没想到张桂芝听后说:“这好办,虽然钱由咱家出,但对外就说姐仨共同操持的……俺也想过了,娘家人都知道俺和大哥的关系,再说大哥卧床几年了,孩子们给他花钱治病掏光了家底,咱出钱来扎纸活请‘响’,侄子侄女们大概也不会反对。”看王清明还想说些什么,张桂芝坚决道:“你不要再忧虑,和姐姐及娘家人协商的事儿,俺来出面,恁只管代表咱家去扎纸活请‘响’就行了。”
王清明依了她,事情就算定了下来。可张桂芝又提出了新问题:“这几天咱们靠在丧事上,真真和娟娟谁来管?咱们不在家,可俩孩子总得要吃饭啊……还有,家里的那头牛和那头驴等牲口,也总不能饿着吧!”
“相比大哥的丧事,其他事都是小事儿!”王清明想了想说,“外甥女娟娟自她爸妈外出打工后,就一直住在咱们家,他爷爷奶奶没操多少心,咱不在家这几天,可请他们来。至于那些牲口,可找李保银来照看嘛,他喂牲口可是个行家。”
张桂芝没再说什么,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于是,夫妇俩按照说的,由王清明给亲家打了电话,说明情况后,娟娟的爷爷奶奶不仅没推脱,反而爽快道:“正想到恁家看望呢,俩孩子交给俺,你们就放心吧。”接着,王清明又去了李保银家,保银老汉也爽快答应了。一切安顿好,王清明便陪着张桂芝,匆匆给大舅哥奔丧去了。
来到张桂芝娘家时,张桂芝的俩姐已经到了。二哥三哥和大哥的两个侄子,正与村里的一些人在灵棚隔壁的小屋里议事。王清明是客,自然不能参与到这种事的商议中——以往来张桂芝娘家时,往往与大姐夫二姐夫一起说话,现在大姐夫已经去世,二组夫偏瘫来不了,他感到有些拘谨,便与张桂芝会同张桂芝的俩姐,一起看望大嫂,并与她商议相关的事情。
张桂芝俩姐也七十好几了,身体精神还算好,她们知道妹妹的经历和性格,因此也像哥哥一样让着她。可在大哥这件事上,她们却有自己的意见,所以当妹妹提出要独自给大哥请“响”扎纸活时,她们立即表示出了反对,而且不仅她们反对,大嫂也不同意。张桂芝有些急了,先劝说两个姐姐,说大姐夫不在了二姐夫又瘫痪在床,家里的光景她是清楚的,大家都是至亲,请“响”扎纸活这事儿,无论谁承担都得来办,自己主动提出来承担,是为了弥补对大哥的情分,当然,即便自己出钱,对外却说是姐几个一块儿办的,想必外人不会说闲话。张桂芝说到这儿,俩姐也不怎么反对了,却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,说请“响”是大头,既然张桂芝提出来操办,那就由她来办好了,但俩姐也不能袖手旁观,至少要出扎纸活的费用。
接着,张桂芝又劝说大嫂,说大哥卧病在床好几年,花费自然不少,家里困难她是清楚的,她这样做是帮助家庭解决困难。大嫂不再多言语,说只要孩子们同意了她就没意见。发丧是件花钱很大的事儿,两个侄子正在为此而发愁,以小姑为首的三个姑姑提出了要出资帮助,虽然名分上有些不合适,但侄子们都是务实的人,家里又实在缺钱,既然母亲不再说什么,他们也最后同意了。
意见定下来后,王清明亲自出面,联系了邻近镇上最有名的姜姓吹响班,又从镇上姚哑巴的纸活店中联系了纸活。吹响班第二天一早就来了。而隔后一天,纸罩、纸屋、纸马、纸人、纸家具和纸花圈等纸活也全部到位。大哥的丧事办得隆重而体面,虽然花了不少钱,但在乡邻面前挣足了面子,张桂芝虽然对亲大哥的去世悲伤不已,但对他丧事的办理却是满意的。
大哥的丧事处理完毕,王清明夫妇回到了王楼村。这天下午,老两口刚进家门,村里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,村长王永全在广播中喊道:“全村老少爷们注意啦,再下一遍通知……”王清明和老伴伸长着脖子听,可他们毕竟年纪大了,耳朵有点背,王清明问老伴:“喇叭喊的啥?”张桂芝皱着眉头道:“好像是农活的事儿,具体我也没听清。”正说着,大喇叭又响了起来,王清明走到院子里。这次终于听清了,只听王永全又喊道:“上面通知,全村各农户,务必这几天将地里的秸秆处理干净,不能遵照执行的,要被点名罚款……”
实际上,王清明夫妇奔丧这几天,王永全在喇叭中已通知几次了。多数农户在秋收之后,已将田地里的大豆、玉米、棉花、高粱等农作物的秸秆处理完毕,目前只剩包括王清明家在内的不多的十几户人家没能完成。按照口头协议,王清明家的农作物秸秆由李保银家来收,以用作补充牲口的饲料。王清明夫妇办完大舅哥丧事回到家天将傍黑,本想晚饭过后,要到保银老汉家问问情况,在感谢照顾牲口的同时,商议着把收秸秆的事给办了,可还没等到晚上,王永全却找上了门来。
看到王清明,王永全便气呼呼地问:“叔,俺在喇叭里通知几次了,为啥恁家地里的棒子桔还不收拾?”
王清明解释:“这几天恁婶子娘家有忧事儿,俺陪着奔丧去了,这不,才刚刚回来。”
“不管啥原因,村委的通知都要认真执行。”王永全冷着脸道,“这次我可是登门通知的,不能再说不知道了吧!”
支书王清河的四个儿子中,王永全的三个哥哥都很有出息——老大在外地为官,老二在县城经商,老三在沿海城市某家公司当部门经理,最小的王永全却没能上成学。王清河夫妇也需要有个儿子照应,于是便让他在家乡发展。家境优越的王永全,从小就调皮捣蛋,在当地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,方圆一带没有人敢惹。他长大后,在父亲的运作和支持下,先是承包了村里的砖窑厂,后来又接替父亲的村长职务。王清河也有意培养他,虽然对他不放心,但除了大事出面外,村务小事儿多由他来处理。
作为晚辈的王永全说话难听,王清明有些不高兴,本想反击一下的,可想了想还是忍住了。他继续解释道:“你是知道我家情况的,多年来俺和李保银家商量好了,秸秆由他家帮着收,这几天俺在外边不知家里情况,正想去他家问问呢,这不,你就来了。”
“李根背部长了个毒疮,去镇医院动手术了。”王永全爆料道,“他父亲年纪大了,还喂养了那么多牲口,一个人哪能忙得过来,还是自家各收自家的吧……”
王清明一惊,本想问问具体情况,但他实在不愿和王永全多说话,便道:“放心吧,这几天,俺一定想方设法,把地里的棒子桔给处理了!”
晚饭过后,王清明怀着疑惑去找李保银,刚进院子,就发现他孙女春草在庭院里哭。王清明抚摸着春草的头问:“妮儿,这是哭啥嘞?”
看到有人过来,春草哭得更伤心了,一把鼻涕一把泪说:“俺爷爷的胃病犯了,在床上痛得直打滚嘞!”
王清明又是一惊,一边安抚着春草一边道:“妮不要哭,快带俺去见恁爷爷!”说着随着春草走进李保银的房间,果然看到李保银脸色蜡黄,额头冒着虚汗,正在床上“嗳哟嗳哟”地呻吟着。
王清明愈发急了,转头又问春草:“恁娘嘞?”
春草哽咽着回答:“俺爸长疮住了院,俺妈带着弟弟猫蛋狗蛋去医院照料去了。”
李保银的病情紧急,王清明安慰一下春草,接着急忙叫来武木匠,两人合力把李保银弄到地排车上,小跑着拉着到了“百济堂”。陶行善给号了脉,又给李保银简单吃了几粒止痛片,然后对王清明和武木匠说:“依我诊断,保银的病情紧急,八成要做手术,还是到大一点的医院吧。”
武木匠历来快言快语,看陶行善不能治疗,不禁嘲讽道:“有人说,恁这中药铺子不如西药的卫生所,看来说得不错嘞!”
陶行善并不生气,把武木匠拉到一边,进一步解释:“保银腹痛得厉害,还伴有恶心干哕症状,看来不是一般的胃病,有可能是‘急腹症’,也就是常说的‘胃穿孔’,需要尽快动手术,可俺这儿的条件是实现不了的。”
武木匠仍然气呼呼道:“嗨,不就是个肚子痛嘛,恁连这小毛病也治不了,还叫‘百济堂’呢,俺看叫‘掰扯堂’得了。”
陶行善不想和他争这个理,再次催促道:“如果真是患了‘急腹症’是等不得的,需要马上到大医院手术,不要瞎白话了,快点出发吧!”
王清明和武木匠不懂医术,看李保银痛得厉害,陶行善又催得紧,于是便听从陶行善的意见,由武木匠开着个农用三轮车,当晚便把保银老汉送进了镇医院。急诊检查发现,李保银果然得了“胃穿孔”,必须得住院进行紧急手术。但是非常不凑巧,镇医院主刀的大夫外出学习了,值班的大夫又做不了,建议转县医院治疗。没办法,两人和之前来住院的李保银的儿子李根说明情况后,又急慌慌把李保银送到了县医院。
路上,武木匠有些懊悔地对王清明说:“在‘百济堂’,俺当时一急,有些错怪行善了,他说得对着嘞!”王清明说:“三百六十行,行行有状元,这道那道各有门道,陶家几代人都经营中药铺,如果没有几把刷子,能经营得下去?”又叹息说,“受西医冲击,中医整体衰落下滑,陶家的中药铺经营越来越差,就像恁家的木匠铺,手工做的再多也比不过机器快,唉!”
武木匠不再作声,眉头紧皱着陷入了沉思。是啊,王清明说得太对了,想想自家的木匠铺,前后的兴衰变化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在王楼村,武姓人家也是外来户。清朝中期,黄河再次决口,武木匠爷爷的爷爷那一代,从淮北逃荒来到了王楼村并定居了下来,至武木匠这一代,在村中也有上百号人了。武木匠的爷爷跟人学习做起了木匠,走村串巷地揽手艺来做。后来他父亲子承父业,在王楼村开起了木匠铺子。武木匠的手艺也是从小跟父亲学的,开始几十年生意还好,只是后来日益惨淡了。
大概因为手艺人有共同的话题,王清明和武木匠很能谈得来,而且两家也经常地互帮互助。王清明五十多年的江米人生涯中,先后用坏了三个江米人木箱,每个箱子都是武家给做的。武木匠有两个儿子大宝和二宝,尽管武木匠也想让俩儿子跟他学木匠,但俩孩子都说做木匠太艰辛,今后也没啥大出息,说啥也不学。不过,令武木匠夫妇欣慰的是,大宝是块上学的料,学习成绩一直很好,后来考上了北京的某所大学,毕业后又考入了北京某机关,现已成了家并定居在北京了。二宝虽然学习也不错,却没有像哥哥一样考入名校,专科毕业后回到了县城,现在于一家私营企业里打工,虽早已到了成家的年龄,却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,对此武木匠夫妇很是发愁。
来到县医院,王清明和武木匠把保银老汉送进了急诊室,并当夜做了手术。待李保银转入病房后,武木匠提出要回去,说提前约定好了,明天上午要给小儿子二宝相亲。武木匠离开后,只有王清明一人留下来照顾李保银。这样他一连照顾了两天,直等到保银老汉的儿媳山茶到来后才得以喘息。
一家有两个病人,而且住在不同的医院,山茶很是着急。王清明觉得,山茶一个外地女人,人生地不熟,必须帮她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。在和山茶商量后,由王清明出面找了住院部领导,协商将动过手术的李保银转到了镇医院。一切安排妥当后,王清明这才回到了家。
在帮保银老汉治疗的这几天,鲁西南大地又来了一场寒流,气温骤降,天阴得厉害,预报要有一场中雨。王清明本想回到家,找些保暖的衣物给李保银父子送去,然后开始外出卖江米人的行程。然而还未进家门,却在村庄的小桥头遇到了神色慌张的唐焗匠。唐焗匠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说:“清明不好了,葛家出了大事啦!”王清明立时紧张起来,瞪着眼睛望着唐焗匠。没等他发问,唐焗匠又喘息着解释说:“是这样,葛老三家的二小子葛存义不见了,全村人正在寻找呢……”
葛存义的祖父是个弹花匠,解放前就已作了古。父亲葛老三也会弹棉花,平时就像候鸟一样,农闲时外出走街串巷,农忙时就回家务农。母亲吴凤英小时候出麻疹落了一脸麻子,平时很凶很强势,按当地的话说有些“口”,常因琐事骂大街,一张嘴便唾沫星子乱飞,村民们便送其个外号“吴麻子”。
葛老三夫妇先后生了七八个孩子,却只成活了葛存义和葛存礼两弟兄。葛家人本来就不旺,在葛存礼上面的几个哥哥姐姐夭折后,为了葛存礼能够存活成人,葛老三便委托王清明的干娘五奶奶来说合,把葛存礼认给了王清明夫妇当干儿。
在当地,认干爹干娘是比较流行的风俗。对一般体弱多病的孩子,或八字较软或五行有缺的孩子,常常让算命先生算过孩子的生辰八字后,给孩子认干爹干娘,以这样的方式冲一下,使孩子能够健康存活。干爹干娘多是孩子较多命运较硬的人。王清明从小多病,又得了小儿麻痹症腿脚不好,但他却存活了下来,还学了江米人手艺,娶了张桂芝这样在县城边长大的漂亮媳妇,并生了一对健康的儿女,这说明他的命硬。因此葛老三在为儿子选干大时,首先想到了王清明。
王清明夫妇知道葛老三家的处境,何况有干娘五奶奶来牵线,于是便愉快地接受了这门干亲。王清明本想叫葛存礼跟他学习江米人的,可江米人手艺要求高,笨手笨脚的葛存礼缺乏灵气,眼睛又不好使,学了几年根本不入道,后来便打了退堂鼓。再后来,葛存礼便干起了粗活,跟了邻村的一位包工头的工程队,并在工程队中跟一位师傅学了泥瓦匠。家境不好,眼有残疾,人又太过木讷,做泥瓦匠名声又不大好听,以至四十大多了,葛存礼还没娶上媳妇,作为干爹干娘的王清明夫妇,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。
相比兄长葛存礼,弟弟葛存义比哥哥小了十来岁,性格却和哥哥大不相同。葛存义机灵活泼,爱说话,也爱闯荡。小时候,拜村里的仝铁匠为师,非常用功地练过几年拳脚,刀枪棍棒都能耍上几下子,身手很是麻利。后来,心灵手巧的他不仅跟父亲学会了弹棉花,还跟一位“篾匠”学会了编篾席、笤帚、柳筐等条编的技艺。除此之外,他也跟王清明学过几年江米人,只是后来社会发生了变化,民间手艺越来越没有市场,于是便放弃了这些民间手艺的学习,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到沿海去打工,主要从事与建筑相关的体力活。
那年秋季,沿海遭遇台风,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被刮倒,有几个民工不幸被砸死砸伤,包工头看势不妙携款跑了,快到春节了仍不见踪影。葛存义等工友们忙活了十来个月,本来要领取工钱回家过年的,可找不到包工头也无可奈何。那段时间他很是郁闷,经常去附近的小饭店喝闷酒。正是这个时候,他认识了刘莲花。
刘莲花也是个苦命的人,爹爹早年得病死了,母亲后来改了嫁,她初中没毕业就跟人来到了沿海打工,过年过节也不愿意回家。随着年龄变化,她出落得愈发漂亮,也越来越受到男人的关注。和天下所有的少女一样,她也有着自己的梦想,希望自己的运气好一点,不仅能找到好点的工作,也能找到称心的另一半。然而,看似繁华风光的大城市,对打工者来说却没有多少好机会。尽管如此,她不想到歌舞厅、会所那些听说不好的场所去。先后换了几个不如意的地方,后来在一家饭店里做服务员。这家饭店不大,消费对象主要是中低档群体。有天来了一帮地痞小混混,见刘莲花漂亮便心生邪念,时不时地对她动手动脚。找份工作不容易,再说刘莲花一个姑娘家也不敢得罪这些人,于是便忍气吞声,只要对方不太过分,她就得过且过了。
这天晚上,葛存义也来这家饭店吃饭。心里烦,他要了瓶廉价的白酒喝。喝到多半斤时,忽见那伙流氓正调戏为难刘莲花。葛存义看不下去,在和混混讲理时发生了争执,继而双方大打出手。有武术功底的葛存义将对方打翻在地,房间被弄得杯盘狼藉,饭店老板报警后,葛存义带着刘莲花逃了出来。不久,走投无路的两人回到了曹南县,并从此过起了小日子。
葛老三家就一处院落,房屋本来就不多,葛存义和刘莲花到来后,家中更显挤巴了。孙子狗狗出生那年,葛老三夫妇东拼西借,在村头讨了块宅基地,为小两口盖起了三间瓦房,把他们分开来单过。葛存义担心自己上了警方黑名单,就没敢和刘莲花办结婚证,小两口也没再外出去打工。一年后,刘莲花生了个大胖小子叫狗狗,小夫妇更是出不去了。尽管分了家,可父母毕竟上了年纪,老实本分的哥哥又挑不起门面,家里许多主意还得葛存义来拿。
在老家这几年,葛存义一开始在本村王清河二儿子办的纸箱厂打工,可纸箱厂环保不达标,后来关闭了。他又到王永全的砖窑厂去揽活,可砖窑厂经营不善半死不活的,一年干干停停挣不了几个钱,他于是又离开了。再后来,他拾起了过去做条编的手艺,农忙时帮着妻子照顾田地,平时在家编些条筐、篮子、扫帚等一些手工艺品,集中起来拿到集市上销售。闲暇时,也会到故道的水库河塘,去采野莲挖野藕或者捕捉鱼虾来卖。当然,如果有其他能挣钱的活计,不管这活多么危险多么繁重,他也会不惜体力地去承接。
刘莲花刚到葛家时,看到破落贫困的光景有些失落,但葛存义对她十分体贴,公爹公婆和大伯哥葛存礼对她也很好,这给了她很大安慰。另一方面,她也慢慢改变自己,努力适应并融入这个家庭中。儿子狗狗出生后,为了多挣些奶粉钱,她在做好家务的同时,也跟丈夫学做些编织的手艺。不仅如此,毕竟是上过几年学又到过城市的人,她并不满足于眼前的一切,就在前年的春天,听说邻近乡镇的一些村庄办起了电商业务,通过淘宝平台做生意足不出门就能挣钱,受启发的她便和丈夫商量,也想借助淘宝来卖编织品。她的想法丈夫也认同,只可惜这个家实在太穷了,没有网络和电脑,也没有相关的设施,想经营电商又如何做得起。
尽管如此,小夫妇并没有失去信心,他们相信只要勤劳持家不断打拼,这个家庭就不会永远地穷下去。他们经常乐观地认为:未来的日子一定是富裕红火的,今后的人生也是丰富多彩的——他们将来会有足够的钱,能使过惯穷苦日子的父母享受清福,能使儿子像有钱家庭的孩子一样上更好的学校……他们还憧憬着,将来一定要为大哥娶个媳妇,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为他举办一场体面的婚礼……
可这一切还未实现,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,作为家庭顶梁柱的葛存义,竟然意外失踪了。这一突发的变故,不仅使这个家庭陷入恐慌和悲痛之中,也将刘莲花对未来的梦想给彻底打碎了。
——就在几天前,葛存义接受邻村一户种藕人家的请求,要他去帮忙到水塘里挖藕。这是一项体力活,也是一项技术活,干一天开一天佣金,根据刨出来的藕的重量开工钱。就在昨天傍晚,挖藕劳累了一天的葛存义回家吃晚饭,喝了半斤白酒后又出去了,说挖藕时看到故道里的芦苇熟了,想割回来让莲花编织工艺品,以换些钱给来年上小学的儿子交学费。刘莲花本来提出要和他一起去的,他没允许,说狗狗还小在家需要照顾。刘莲花也没强求,只是提醒他注意保暖和安全,她在家里等着他回来。狗狗睡去后,刘莲花仍在等,谁知等到了半夜也没见他回来,打他的手机也不接,下半夜又到村头迎了几次也没见到人,刘莲花有些慌了……这样一直忐忑不安地等到第二天黎明,感觉不妙的刘莲花去见公公婆婆和大哥葛存礼,将情况告诉他们后,一家人按昨晚葛存义所说的劳动地点寻找,发现水库里只有他家的那只小船,近水旁有一大片砍倒并捆好的芦苇,却没有看到人……
得知这个意外后,王楼村像炸了锅,先是葛家周围的邻居们自发地参与到寻找之中,然而能找的地方都找了,仍未见葛存义的踪影。王清河、王清田和王永全也听说了情况,也先后来到葛家,组织全村的人去寻找,然而一拨又一拨寻找的人派了出去,却一拨又一拨地失望回来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希望越来越渺茫,整个王楼村弥漫着一团悲伤郁闷的气息。
对葛存义的失踪,最为焦急伤心的还是葛家人——哥哥葛存礼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,在葛存义曾经走过的路上来回寻找着,也来到昨天弟弟去过的芦苇荡,一遍遍地用木棍往水里试探着……父亲葛老三越来越失望,七十多岁的他再也走不动了,被人搀扶着回到家里,圪蹴在堂屋的角落里,不停地吸烟和叹息,脸上的皱纹如枯死的老树皮般更显干瘪了……母亲吴凤风也出去寻找了,失望的她瘫软在了故道内的藕塘边,被人抬回家后便掉了魂般,在床上躺着一声高一声低地哭喊着:“俺的小啊,恁不在了这个家可咋弄呢……俺的爹、俺的娘啊,恁救救苦命的俺吧……老天爷,老地爷啊,恁都长长眼吧,如果俺的命能换回小的命,就把俺的命来换吧……”
此时的刘莲花更是惶恐到了极点,她望着还不懂事的儿子狗狗,一边等待着消息一边不停地流眼泪。丈夫的失踪,对她来说仿佛天塌地陷了一般,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她感到快要崩溃了,身体轻飘飘的,似乎一脚踏进了一口深不可测的黑洞,急骤地往黑洞的深处滑着、滑着……孤独无助的她,在坠落中拼命地想抓住某种东西,遗憾的是什么都无法抓得住……
又过去了半天,去搜寻的人一个个地回了来,所带回的信息仍然令人失望。支书王清河的脸变得越来越青,时不时地训斥说话不当的人。大家有些怕他,便不与他搭话,有的还故意躲着他,将情况向脾气随和的王清田来说,这更令王清河感到尴尬和愤怒,使本来就显长的那张老脸,现在难堪的更像个猪腰子了。
不久,村长王永全骑着摩托车而来,与他同来的还有村会计黄学文。他们来到葛家后,没等王永全说话,黄学文便有些胆怯地向王清河汇报说:“我和永全哪里都找了,却连个人影也没见到!”
“什么哪里都找了?故道内外的河流、池塘、水库、潭坑,附近大小十几个村子,都去找过啦?”王清河怒斥问。
“这么多地方,又哪能找得个完!”看父亲责问黄学文,王永全忙凑上来说情,“再说,葛存义他……说不定死到哪去了呢……既然死了,就不要再找了嘛!”
“混账!”王清河不容分说,一个巴掌甩到王永全的脸上。随口又骂道:“狗日的你还是村长呢,村长哪能说出如此胡话来!”
王清河心里郁闷着,将所有的怒气都用在了巴掌上,因此这一巴掌甩得很重,把王永全差点给打懵了。王永全捂着发烫的腮帮子,眼睛瞪得老大,一时不知说何才好,他不相信,父亲会突然当着这么多的人揍他……黄学文虽然没挨揍,却也一样懵圈了,反应过来,赶忙拉着王永全要离开。王永全捂着脸一边往外退,一边对父亲表示着不满:“打人算啥本事,有能耐,自己去找啊!”
突然发生的一幕,令现场气氛极为尴尬。众人出来打圆场,却不说王清河这一巴掌打得对不对,只是说些胡乱的话。有的说:“大家不要没了信心,再坚持坚持,或许就能找到了的!”也有的说:“是啊,葛存义平时接活多,又好喝酒,说不定到哪里接了活干,或躲到哪里喝酒去了呢。”还有人甚至说:“也许他干活太累,找个地儿睡觉去了,醒了自然就会回来的……”
对大家的议论,王清田都认真地听,沉默了会儿,对王清河小声道:“你是支书,全村人都看着恁嘞……你不要急,更不能动手打人……何况永全还是村长,你打了他,他今后在村里如何见人?”
“正因为他是村长,我才打他嘞!”王清河仍然发着火道,“俺打他,是要给他长个记性,叫他以后知道,哪些话该说,哪些话不该说!”
王清河说着,气呼呼地披上马褂要离开。他咳了一口浓痰,擤了两把鼻涕,在鞋帮上蹭了一下,歪歪斜斜地往外走。跨出葛家的院门时,又甩下一句:“我要亲自找,俺就不信,葛存义他小子能钻到地缝里去……”走了几步,又狠狠地说,“即使钻到地缝里,也要把他给挖出来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