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启五年七月初四,米脂书铺。
徐晨带着贺老六和秀娘刚进门,就撞上正要外出的东叔。
老头子看着跟在徐晨身后、瘦得像根豆芽菜的小丫头,眉头皱成疙瘩。
秀娘吓得抄起门边扫帚,拼命扫地,头都不敢抬。
东叔长叹一声,指了指门外:“晨哥儿,这边每年卖身为奴的,没有一万也有八千。
光米脂县,飘香院那样的地方就收了上百个孩子。你救得了一个,救得了所有?”
徐晨默然。
他刚和秀娘聊过——飘香院后巷那个小院里,还关着十几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女童。
有的是家里欠债被卖,有的是灾年活不下去被爹娘送来,还有的干脆就是人贩子从路上拐来的。
他能赎一个秀娘。
但他能把飘香院拆了吗?
能把整个陕西的青楼都砸了吗?
现在不能。
“能救一个,是一个。”徐晨最后只吐出这六个字。
东叔看着他,眼神复杂:“做事要量力而行。你连日施粥,已经让本地乡绅不痛快了。
县衙的粥棚这两日就要停——你那点银子,养得活上千流民?”
徐晨听懂了弦外之音。
他施的粥“插筷不倒”,县衙的粥“清可见底”。
流民不是傻子,对比太鲜明。
本地乡绅本想靠施粥赚点名声,现在全成了骂名。
更关键的是——原本流民在米脂吃几顿稀粥,啃完草根树皮,就会往南迁移。
现在因为他天天供稠粥,流民全聚在城外不走,人数还越来越多。
这是在米脂县埋雷。
一旦他供不起粥,饿疯了的流民会做什么?
抢粮?
暴动?
围攻县城?
米脂县的官绅老爷们,夜里睡得着觉才怪。
“侄儿有办法。”徐晨抬起头。
东叔不信:“上千张嘴,你能有什么办法?”
“建纺织厂。”徐晨吐出四个字,“招他们做工。”
东叔愣住,随即失笑:“纺织?一台纺车才雇几个人?你那是杯水车薪!”
“不是小作坊。”徐晨目光沉静,“是江南那种几百人的大厂。江南能做到,陕西为什么不能?”
东叔盯着他看了半晌,忽然压低声音:“难不成,你真是松江徐家的人?”
徐晨可不接这茬,但是挂着个江南富商的名号总是好做事。
他回道:“三日后,请东叔来看一样东西。”
七月初四夜,书铺后院。
烛火通明。
贺老六抡着锤子,“砰砰砰”敲打木架。汗水从他额角滑落,他随手抹掉,眼睛盯着手里正在组装的部件——那是徐晨画的“珍妮纺纱车”骨架。
旁边,小五和秀娘围着一个大木桶,正用草木灰水拼命搓洗羊毛。
膻味混着碱味弥漫开来,秀娘被呛得咳嗽,手上动作却没停。
徐晨蹲在院角,正跟一把铁梳较劲。
他脑子里反复回放着穿越前看过的那个视频——《穿越必备:从零开始搞纺织》。
Up主说得轻松:去油、梳理、纺线、织布,一条龙搞定。
真上手才知道——全是坑。
光是这把用来梳理羊毛的铁梳,他就改了四遍。
第一次齿距太密,羊毛卡死;
第二次太疏,根本梳不顺;
第三次硬度不够,用两下就弯;
现在这第四把……
“东家,梳好了。”贺老六递过来一根木杆。
徐晨接过来,把晾干的羊毛缠上去,开始手工梳理。
粗糙的羊毛纤维在铁齿间被拉直、捋顺,渐渐变成蓬松的毛条。
半个时辰后,他手里多了一团灰白色、看起来有点脏的毛絮。
“秀娘,”他喊,“会纺线吗?”
秀娘小跑过来,接过毛条,熟练地捻起一端,缠在从街面买来的旧纺车木锭上。
右手摇动车柄,左手引着毛条——一条粗细不匀的灰线,慢慢被纺了出来。
“成了!”小五第一个喊出来。
徐晨长长吐了口气。
徐晨是互联网时代的人,动嘴能力多过动手动手能力,这次的实验让徐晨明白什么叫,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
一个简单的毛纺业都有这多的技术难题,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遇到的问题,徐晨简直不敢想象。
翌日,贺老六把纺纱车也给打造好了,徐晨他们把招准备好的毛条一个个挂在锭子上。
贺老六再一拉毛条瞬间变得稀疏起来,小五摇动手柄,20个锭子同时转动起来,一条条纱线就这样被纺出来。
“先生这个纺纱车太厉害了,居然可以同时放20条纱线,您真是诸葛在世,上知天文,下知地理。”小五钦佩道。
“让俺自己来。”贺老六也充满笑意,羊毛不值钱,但纱线就值钱了,一斤棉花纱线值60-70文,羊毛纱线,价格即便比低,但赚的也比棉纱线要多。
徐晨也露出笑脸,虽然纱线还不均匀,但它效率快,即便是现在的品质还不高,但用来做毛线却是绰绰有余的,而且也可以纺织成毛毯,只要价格足够低,就不用担心销量。
前院正在核对账本的东叔听到动静,快步走进后院。看见那台同时吐出二十根纱线的纺车时,老头子的胡子都翘起来了。
“这……这是……”
他冲过去,捏起一根刚纺出的毛线,对着晨光细看。线不够匀,颜色也灰扑扑的,但确实是能用的纱线。
东叔猛地转头看向徐晨,声音发颤:“一斤羊毛三文,一斤棉纱七十文……十倍的利!晨哥儿,你这纺车要是传出去——”
“所以不能传。”徐晨打断他,“至少在咱们站稳脚跟前,不能。”
东叔重重点头,眼里冒出精光:“你要的纺织厂,老夫入股!”<br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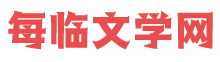
 连载中
连载中 




















